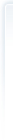
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3.12.02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2年度面上项目“整体政府视角下的中国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研究”(71173004)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循证决策是十多年来国际公共政策领域的热门实践,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缺憾。主要内容包括:循证决策出现的背景及其在学术界和政府管理中的地位;循证决策的内涵和构成要素;循证决策的理论渊源及其特征;最后,围绕定位、相关争议、研究关注点三个方面,讨论如何认识循证决策。
[关键词]循证决策;循证型政策;符号型政策;决策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12-0023-06
十多年来,“循证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循证决策)一直是国际公共政策领域的热门实践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相比之下,国内的相关研究还相当薄弱:循证原则和循证决策在医学、教育、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应用成果相对丰硕,公共政策领域的系统研究成果如凤毛麟角,而且在内涵、特征、定位等方面存在一些待商榷之处。本文从出现背景及其地位、内涵与构成要素、理论渊源及其特征、如何认识循证决策等方面进行系统讨论,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一、循证决策出现的背景及其影响
循证决策的理念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布莱尔政府,虽然学界对此尚存争议。1999年,布莱尔政府公布了《政府现代化白皮书》,在明确政府的未来愿景和核心目标的基础上,白皮书提出了五项关键承诺或政府现代化的五个着力点,其中第一个着力点即突出公共政策的战略性和前瞻性,力戒决策碎片化或成为现实压力的被动应付。为此,白皮书提出了确保公共政策的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七条“核心原则”:(1)围绕共同目标和明确界定的结果设计制定政策,而非囿于组织结构和职能分工,从而保证决策中的跨部门协同;(2)充分考虑多种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期望,保证公共政策的包容性;(3)注重成本/收益分析和影响评估,避免简单化管制给企业增加不必要的负担;(4)改变被动防御心态,构建相应的渠道和机制,推动政策制定中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通过协商改进政策;(5)借鉴风险评估、管理和交流方面的最佳实践,提高风险管理水平;(6)前瞻性和开放性思维,视线超越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向其它国家学习经验,将欧盟和国际标准融合到政策制定中;(7)从经验中学习,将政策制定视为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改进理论研究成果和证据的使用,强化改革创新试点的评估、反馈和应用。
如果说《政府现代化白皮书》中“改进证据的使用”体现了循证决策的思想,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室同年发布的《21世纪的专业政策制定》,则明确使用了循证决策的概念。该文件指出,政府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驱动力是公共服务供给和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制定,并将“使用证据”看作是提高政府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按照该文件,循证决策意味着:“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倡议)是建立在最佳的可利用的证据的基础上,这些证据来自一系列广泛资源;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在政策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参与进来并且经历整个政策过程;所有相关的证据,包括那些来自专家的,都会以一种重要的和通俗的格式提交给政策制定者”。[1] 2000年,英国绩效创新中心在其报告“合力致胜”(Adding It Up)中分析了数据分析与模型建构在决策者获取证据中的重要性。2001年,英国政府绩效与政策研究中心(CMPS)颁布了一份报告“更好的政策制定”(Better Policy Making),主要通过案例研究考查了政策决策者利用证据的方式,分析了部门所利用的证据的关键来源,包括“国内和国际的研究的数据、政策评估、经济模型和专家知识[2]”。至此,“循证决策”不仅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和外延的专门术语,而且形成了由特定内容要素构成的体系,并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高度关注。
学界对循证决策的关注首先表现为专门研究机构和交流平台的大量涌现,如: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证据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vidence and Policy);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提供130万英镑的资助,由证据与政策研究中心设立的“证据网络”(Evidence Network);美国“坎贝尔协同研究中心”(Campbell Collaboration),它侧重社会和教育领域,系统审视最佳证据并分析相关政策和实践的实际效果和影响;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致力于“结果映射法”(Outcome Mapping Approach)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跨国性“循证政策开发网”,由20多个机构成员和数千名实际工作者组成,重点是研究循证决策的程序以及实用工具;“循证型政策联盟”(Coalition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等。
此外,学术界对循证决策的关注表现在学术活动的活跃和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英国学术界于1998-1999年间召开了三次重要的大会,重点探讨循证决策的相关问题;海外发展研究所为了完善和推广其“结果映射法”,迄今已在全球范围内举办了40多场工作或培训会议;坎贝尔协同研究中心则制作了50个循证决策的成功范例。上述关于研究机构、交流平台、研究成果等事实和数据,除特殊标明者外,均来自维基百科循证政策词条。http://en.wikipedia.org/wiki/Evidence-based_policy.至于学术研究成果,从时间看,1999年前,只有少量关于循证决策的研究,且主要集中于医疗卫生领域,有数据为证:将“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输入SAGE(1999年前),只有4篇相关文献,且都是循证医学领域的。1999年后,学界对于循证决策的关注度提升,相关研究文献大量涌现,文献量达到280篇(截止到2013年10月),其中属于公共政策领域的文献约占30%。
至于循证决策在实践中的地位,除首推者英国政府外,其他国家同样给予高度重视。2008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指出:决策需要有效的方法、高质量数据、经得住检验的证据,而这些又需要时间、高素质和独立品格的决策者以及宽松的决策环境。他宣称:“循证决策居于创新型政府的核心”。[3]
各国不仅倡导循证决策的理念,而且为此提供了组织保障。英国内阁办公室在合并文官学院的基础上,于1999年成立了“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其核心任务是“寻求获取与吸收能够发现的最好的研究证据与管理实践”,从而确保“政策和行动以明智的证据、连贯的思考和牢固的顾客导向为基础”。[4]在美国,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多年来鼓励运用随机试验、准试验设计等方法来获取评估数据,包括历史绩效数据、年度绩效计划与报告、财政报告等数据。2002年,美国教育部建立了有效教育策略资料中心,主要目的是推动教育研究的证据科学化,“在教育领域中为教育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公众提供一种中央级别的科学而可靠的证据资源”。[5]为促进不同政策领域的最佳实践以及部门之间的数据分享,发达国家政府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分享机构。比如欧洲国家设立了国家调查数据档案馆;南非在开普敦大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研究基金南非数据档案馆”。
二、循证决策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与“循证决策”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循证型政策”,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政策制定可以视为一种活动或过程,如果这一活动或过程中严格遵循基于证据的原则就是“循证决策”,其产出就是“循证型政策”。换言之,循证决策着眼于决策过程,而循证型政策着眼于其产出。简单起见,本文的讨论不对这两个概念做严格区分。
何谓循证决策?Sanderson认为,循证决策的核心是“使政府的政策行动更具理性,在更大程度上建立在‘明智证据的基础上’”。[6]在Davis看来,循证决策就是决策建立在经过严格检验而确立的客观证据之上,“通过把可能获得的最佳证据置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核心位置,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7]他认为EBMP是一种“兼具战略性和操作性”的活动,其部分功能是为未来决策者提供证据基础。Sandria Tennant和Anthony Clayton 认为:循证决策包括系统严格的方法及理性分析,决策过程中增强专业知识的运用,从而实现最优项选择。循证决策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政策干预产生最佳结果,同时提高政府的有效性,减少资源浪费,使得公共支出“物有所值”。 [8]
为什么需要推进循证决策?学者们提出了六条理由:(1)政策过程高度复杂而且多数非线性,简单地提供相关信息,进而期望决策者据此行动基本上行不通;(2)由于信息鸿沟的存在、政府透明性不足、快速反应的需要、政治方面的考虑,加上决策者很少是科学家,许多现有政策多不是以证据为基础;(3)基于科学研究的证据可以大大提高决策质量,对人民生命产生巨大影响。比如英国海外发展署基于科学研究的干预政策,在加纳成功把受艾滋病感染的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43%;(4)对政策实施环境的全方位、深入了解显得越来越必要和迫切;(5)政策创新者需要新的技能以便对决策实施影响,包括政治技能、沟通技能、整合技能等;(6)政策创新者需要有强烈意识并安心于自己的角色:从研究者到政策创新者、从研究机构到政策咨询思想库,意味着从学术研究到政策介入的巨大方向性改变,相关主体的职业兴趣和成功评价标准必须随之改变,并要掌握沟通、多学科合作、团队协同等技能。
关于循证决策的构成,Sanderson提出两个关键要素:一是“证据的特质”,即证据从社会研究和评估中获得,具有科学性和高质量;二是证据在政策制定中能够被实践者和专业人员充分有效使用。[9]关于证据的特质,《21世纪的专业政策制定》对其做了说明:“证据的原始成分是信息。高质量的政策制定必须依赖高质量的信息,高质量的信息来源广泛——专家知识、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现存数据、利益相关者咨询、对先前政策的评估、新研究成果,也包括网络在内的二手资料等。证据也能包括对咨询结果的分析、政策选项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及经济或统计模型分析的结果”。Davies强调,证据须经科学研究获得,涉及经济、伦理、社会诸方面,具体如客观影响方面的证据、描述和分析性证据、统计模型、政策的成本/收益或成本/效益分析、相对有效性证据、人们的认知和体验等。[10]Andrew Wyatt等人把通过系统研究得到的证据称为“外部证据”,强调外部证据和其它类证据的结合,包括个人经验、专家知识、咨询结果、政治判断、信念、规范和价值观等等。[11]
梳理上面的讨论,我们把“证据的特质”归结为四个方面:(1)证据不同于信息,信息经过科学加工才能构成证据。除系统科学研究的成果外,证据还包括个人经验、专家知识、政治判断、信念和价值观等;(2)从信息到证据的转换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官员,需要研究者的深度介入,需要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和工具;(3)证据的来源必须广泛,需要对现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搜集、梳理和甄选;(4)证据要具有科学性和高质量。
循证决策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是证据在决策中的充分有效使用。证据本身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在决策中得到有效使用,因为证据很多时候表现为学者的研究数据和研究成果,决策者不一定能充分接触到这些数据,或者不一定能全部看懂这些研究成果与数据。对此Matthew Quinn强调,“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制定以合作为基础,需要有科研机构来提供切实可行的证据,政府需要与科研机构、企业加强合作。”[12]《21世纪的专业政策制定》中就此做了系统讨论:(1)为了保证其有效性,证据最好由那些与决策者具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专家来提供,或者由他们来进行诠释;(2)所有相关证据,包括那些来自专家的,都应以一种通俗的格式提交给政策制定者;(3)要确保政策制定中证据的有效使用,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提高部门有效使用证据的能力;二是提高政策制定者全面了解和有效利用证据的能力。
为提高这两种能力,《21世纪专业政策制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1)部门研究战略:各部门应围绕《公共服务协议》中确立的优先项和重要目标,通过顶层设计构建一体化的研究战略。这一战略应满足以下要求:时间跨度超越任何一个年度开支评审,甚至跨越一届议会的任期;围绕部门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提供专业知识,为政策制定提供长久的支持;在确保部门统筹研究工作的同时,给下属单位留下因地制宜的空间。
(2)跨部门协同:部门各自独立制定研究战略远远不够,需要实现跨部门协同,避免重复劳动和研究水平上的巨大差异。跨部门协同应在各部门明确研究战略的基础上进行,建立跨部门协同的组织机制,强化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
(3)智慧型客户:循证决策的前提是决策者能理解一些特殊的技术研究。政府部门要保持“智慧型客户”的角色,善于吸引并充分调动专家的积极性。具体措施包括:广揽人才,吸引专业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鼓励外部专业人才到相关政府部门兼职;为专业人才开辟特殊的职务晋升通道,改变与行政类公务员竞争中他们所处的不利地位;强化公务员培训,提高他们在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利用专家输入的能力。
(4)经济模型:为解决对部门在关键政策领域经济建模能力的担忧,内阁办公厅绩效创新中心(PIU)正在进行一项专门研究,确认各自的优势和弱点并提出改进建议。该研究考虑的重点问题包括:专家与决策者的有机整合;招募一流专家目前面临的主要障碍;研究资金使用中优先项选择的标准和程序。这项研究的结果将为部门提供实践指南。
(5)证据的可及性: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证据的可及性和“用户友好性”:卫生部门建立一个国家卫生电子图书馆,为医疗机构最好地接触到现存的知识提供了更便捷的通道;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招标建立一个国家级“循证政策研究中心”,成功中标者有义务建立一个国际合作网络,即连接不同政策领域的扩展的数据库系统,包括来自美国、英国、欧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的研究综述和政策评价;内阁办公厅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与“循证政策中心”通力合作,推动各部门鼓励积极开发并充分使用数据库。
(6)“知识池”建设:知识池的格式标准由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设计,第一步由各个部门自己建设,其主要内容包括:新政策新项目的目标体系,按结果或按部门进行分类;项目影响评估的结果;相关咨询文件及其反馈信息;所用证据的细节;政策效果评估的细节。随时间推移,这将形成一个成功和失败的历史性记录,健全目前远非完善的“组织记忆”。按照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的设想,知识池最终将包括:一个跨领域政策专业知识的综合目录;现存政策议程的“地景图”;一个服务于政策制定者需要的资源中心;跨部门的研究和评估机制。
(7)研究者角色:知识池建设是一项中长期目标,目前工作重点是强化部门的研究者角色。具体措施有:强化现有相关人员搜集证据的能力,包括首席信息官、图书管理员和政策分析人员;通过开辟职务晋升的快速通道,吸引专业研究人员并保证他们安心工作;促进研究人员间的人际交流或通过电子媒介的交流;鼓励研究者接触一线工作者,因为一线执行者往往比决策者更明白真实情况,更清楚先前的政策为什么会失败。
除循证决策构成要素的讨论外,一些学者还把这些要素与政策过程结合起来。在其颇有影响的专著中,Pawson提出了循证决策的三段法:一是政策理论的阐述与明晰化,即明确支撑特定政策的规范和因果假设;二是验证这些假设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三是在验证基础上对政策理论进行修正。[13]显然,Pawson的理论仅覆盖决策阶段且侧重研究方法。从英国和澳大利亚相关应用案例中可以看出,循证决策贯穿于公共政策整个生命周期,循证原则主要体现在政策过程的三个阶段:问题确认或议程设定以证据为基础;政策方案选择以证据为基础;政策评估和调整以证据为基础。[14]
三、循证决策的理论渊源及其特征
在国际相关文献中,循证型政策是作为“符号型政策”的对立物或替代品出现的。鉴于此,本部分首先讨论符号型政策的概念及特点,通过比较展示循证型政策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追溯循证决策的理论渊源,讨论它与理性决策理论之间的承继与区别。
“符号型政治”和“符号型政策”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在1964年出版的著作中,Edelman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政治:“竞技体育政治”和“有组织群体用以获得具体的、可感触的收益的政治活动”。竞技体育政治就是符号型政治,目的仅仅是赢得喝彩而非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在他看来,政府就是由一系列政治符号构成的复合体,政府官员具有唤起和调动大众情绪的能力;利用特殊地位和环境、语言和构建问题的特有方式,他们有能力赢得支持但不必付出切实努力。Edelman指出了符号型政治的两种功能;一是动员功能即动员大众以赢得支持;二是简约功能,也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对大众产生诱惑力和号召力。[15]综合Edelman和其他学者的观点,符号型政策具有几大特征:(1)宣传鼓动色彩浓厚,目的是靠外在表象来迷惑和吸引人;(2)无视相关政策是否能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关注焦点是其曝光度;(3)用操纵和欺骗伎俩取代具有实质内容的辩论,愚弄公众、隐瞒内情、消解社会公信力,因而在道义上值得批判;(4)口惠而实不止,政策对非组织化群体没有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许多情况下,符号型政策并非决策者有意为之,而是多重约束下的无奈选择。为避免确认决策者真实动机的难题,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了符号型政策的“客观标准”或特征:(1)政策高度简单化;(2)无视环境特征和条件约束;(3)没有经验分析;(4)政策效果有利于精英而非弱势群体。
不论仅从客观标准着眼还是兼顾主观动机,符号型政策的核心功能是大家公认的:政治家借此展示他们的关切并赢得支持,同时免除他们采取切实行动的义务。[16]作为符号型政策对立物和替代品,循证型政策的精髓可以用《政府现代化白皮书》中的一句话来概括:“行之有效才是硬道理”(what matters is what works)。两者的区别用不着太多笔墨。
循证决策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其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因此,考察循证决策的理论和实践渊源,既要搞清楚相互之间的连续性和承继性,又要确认其特殊性,或者说它的发展和进步。如果把政策分析广义界定为提供“与决策相关的知识和政策过程的知识”,那么这一活动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的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被有意识发展,因此能对知识和行动之间的联系进行明确和反省式检验”。现代意义上理性决策的努力出现在19世纪,这得益于经验研究的发展、政治稳定性的提高、专门知识的出现。[17]直到20世纪中期,归功于Harold D. Lasswell的开创性贡献,公共政策得以从政治系统一种产品的身份上升成为一门“政策科学”。Lasswell是通过阶段式的“政策过程”来表达政策科学概念的,即某一既定政策被提议、检验、执行、评估以及最后被终止的程序。[18]政策过程理论实质上继承了科学管理时代的理性决策思维,表达了试图通过改进政府获取信息的质量来改善治理的愿望。这一持续努力的结果,形成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主义模型或理性优化模型。信息在理性决策模型中占据核心地位,所以理性决策模型亦称“以信息为基础”(information-based)或基于信息的政策制定。
循证决策的概念源于循证医学。“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运动始于1992年,“从临床实践中确定一种特定的临床问题……,寻找和评估与特定临床症状相关的证据,然后将这种证据应用到治疗上”。[19]借鉴循证医学完善公共政策的想法始于1996年,在就任英国皇家统计学会主席的演讲中,Adrian Smith对公共决策过程提出质疑和批评,建议“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制定政策。1998年9月“循证决策及其实践”学术会议在英国举办,标志着循证决策概念的正式出台。
可以看出,循证决策承袭了理性主义传统:理性主义是其理论渊源,理性决策模型指导下的相关努力则是其实践基础。下一个问题是:循证决策与传统理性主义的区别何在?基于前面几部分的讨论,循证决策的特征或对传统理性模型的“超越”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1)强调“信息”向“证据”的转换:理性主义模型以信息为基础,由于政策过程高度复杂且许多非线性化,仅仅提供相关信息期望决策者据此行动行不通;信息只是证据的原始成分,循证决策需要信息向证据的转化,从而为决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2)信息向证据转换的制度建设:各部门顶层设计构建一体化的研究战略,在此基础上建立跨部门协同的组织机制和沟通渠道,实现研究战略的跨部门协同,避免重复劳动和研究水平上的巨大差异。(3)循证决策的能力建设:包括部门和决策者全面了解和有效利用证据的能力,具体措施如广揽专业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或者到相关政府部门兼职;开辟职务晋升的快速通道,保证他们安心工作;通过培训等强化现有相关人员搜集和使用证据的能力。(4)证据基础设施建设: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证据的可及性和“用户友好性”,包括数据库和国际证据网络建设,统一内容和格式标准的“知识池”建设等。
上述四个特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信息和证据的区分以及信息向数据转换的重要性,二是实现这一转换的制度、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
四、如何准确认识循证决策?
这涉及三个问题:循证决策是一种理论模型还是一种实践运动?如何看待循证决策受到的批评?我们应从国际循证决策实践中学习什么?
第一,循证决策是一种理论模型还是一种实践运动?国内屈指可数的相关研究中,循证决策更多被视为一种理论模型。郭巍青教授认为:“理性主义决策模型和反理性主义决策模型是政策制定方法论上对立的两极。在它们之间或者之外,至少还有两种重要的模型,一个是渐进决策模型,一个是循证决策模型,前者是从理性主义向反理性主义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环节,后者则是对理性主义决策原则的回归”。在他看来,循证决策代表了理性主义决策观念的东山再起,但又不是传统理性模型的简单回归,它在四个重要方面“刷新和深化了理性决策的命题”:(1)强调“证据选择”,这比理性模型中的“方案选择”更为深刻;(2)将知识运用视作复杂组织背景下的系统工程,将“渐进决策”模型和“垃圾箱”模型所主张的“行为者分析”和“制度分析”纳入考虑,因而是一个重要进步;(3)突出决策信息化、民主化和知识化;(4)突出政策评估对正确决策的重要作用。[20]
我们认为,循证决策不是一个着眼于规约或解释的理论模型,更多是一种政策主张,或者旨在提升政策有效性的“实践运动”。借用郭巍青教授的话:“不是课堂上的教学模型,而是一种‘政府主张’”。称之为“实践运动”有几个理由:(1)其倡导者是布莱尔政府,主要载体是政府官方文件,核心内容及构成要素侧重于实践应用;(2)虽然提倡者区分了信息和证据并强调转换的重要性,但没有对这一区分和转换机制做出系统精致的理论分析,其主要精力在于为实现这一转换以及证据的有效使用构建制度保障和相应的机制。如果把循证决策定位于突出决策科学性和理性的实践运动,它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就既非传统理性模型的简单回归,亦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决策模型“之间或之外”的某种事物,而是传统理性模型的新发展。更准确地说,它承继了理性主义模型的理论逻辑和传统,但在实践上有一定的发展和超越,可以说理性主义的新阶段或者理性模型指导下的实践新趋势。
第二,如何看待循证决策受到的批评?循证决策在学界存在争议和批评。争议首先涉及布莱尔政府是否言行一致的问题:英国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介入伊拉克战争,被学者称为“基于政策的证据”而非“基于证据的政策”。当然,批评主要来自于学界,由于其管理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取向,循证决策受到来自后实证主义的批判,作为循证决策基石的证据也成为争议的焦点。[21]比如,证据是否无可争议?证据是否过于简单化从而脱离政治现实?是否所有研究成果具有同等质量足以构成科学决策的证据?实证研究是否给予对立观点同等的关切?实证研究费时费力,其研究结论对决策来说是否为时已晚?[22]Mulgan指出,把证据置于决策的核心位置是一种误区,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知识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受到学科视野的限制;决策不仅需要证据,而且要考虑其他多种因素;政策不仅要行之有效,还要看付出多大成本;循证决策取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地位,但习惯和传统其实在发挥重要作用。[23]可见,争议和批评的重点不是否定其正当性,而是质疑其可行性和真诚性。对此我们的看法是:不能因为达不到理想状态就否定努力的大方向。
理论上看,循证决策受到的批评和理性主义模型的命运相似。我们认为,在诸多决策模型中,区分应然规范模型和实然经验模型尤为重要。传统理性主义属于规范模型,关注的是应该怎样做,而渐进决策模型、垃圾筒模型、精英模型等属于经验模型,是对现实的描述和解释。不能因为难以达到理想状态就否定原则和规范本身,否则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理性主义模型备受抨击,但依然是各国政府决策的不懈追求。
第三,对循证决策应该关注什么或从中学习什么?如果把循证决策更多视为一种实践运动,那我们关注的重点就不应该是其理论贡献,更不是它与其他理论模型的比较。循证决策承继了理性主义模型的理论取向和逻辑,其主要超越和进展主要表现在实践上。如果说它是一种新理念和新原则,其新颖之处并没有全面超越理性主义。但是,特殊的时代背景、针对的特定情境、新背景下的特殊体现方式、不同的社会效果等,往往会赋予老的理念和原则以新的内涵,使之成为“新”的原则。因此,理解和领悟循证决策,必须把它置于独特的历史背景中,必须深入了解它在政府改革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方式。我们的结论是,未来对循证决策的关注和研究,应该着眼于实际应用的具体案例,从中能获取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Strategic Policy Making Team Cabinet Office. Professional Policy Mak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ttp://dera.ioe.ac.uk/6320/.
[2][4][11]Andrew Wyatt.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The View From A Center.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002(03).
[3]Rudd.K. Address to Heads of Agencies and Members of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http://www.apsc.gov.au/media/rudd300408.htm.
[5]Carolyn J. Heinrich. Evidence-based Policy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in Two Parallel Movements.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7(03).
[6][9]Sanderson.Iran. Making Sense of ‘What works’: Evidence Based Policy Making a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002(03).
[7][10]Davies.PT. What is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1999(03).
[8]Sandria Tennant, Anthony Clayton. The Politics of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 A Case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2(13).
[12]Matthew Quinn. Evidence Based or People Based Policy Making? : A view from Wales.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002(03).
[13]Pawson R. Evidence-based Policy: A Realist Perspective. London: Sage, 2006.
[14]HM Government. Reaching Out: An Action Plan on Social Exclusion. http://dera.ioe.ac.uk/6350/.
[15]Edelman.M.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4.
[16]Schneider AL and Ingram H.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arget Populations: Implications for Politics and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3(02).
[17]威廉·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谢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0-48.
William N. Dunn.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Xie Mi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40-48.
[18]Lasswell. Harold D. The Decision Process. College Par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Press, 1956.
[19]Davies, H. T. 0. and Nutley, S. M. The Rise and Rise of Evidence in Health Care. Public Money and Management, 1999(05).
[20]郭巍青.政策制定的方法论: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J].中山大学学报,2003(2).
Guo Weiqing. Approaches to Public Policy Making: Rationalism and Irrationalism.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03(02).
[21]王哲.循证决策:当代公共政策制定的新原则[D].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Wang Zhe.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A New Principle of Contemporary Public Policy Making. Dissertation of Master Degre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09.
[22]Davis HTO, Nutley, S and Smith, P(ed). What Works? Evidence-based Policy and Practice in Public Services.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2000.
[18]Mulgan G. Government: Knowledge and the Business of Policy-making. Canberra Bulleti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3(04).
(作者:周志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871;李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Evidence-based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Academic Orientation
Zhou Zhiren Li Le
[Abstract]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is a popular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for more than 10 years, domestic research is relatively weak. This paper aims to compensate this shortcoming.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the background of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the connotation and elements of evidence-base policy making,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Finally, the paper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related to the positioning, dispute and research focus and discusses how to make sense of the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Key words]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evidence-based policy, symbolic policy, scientific decision
[Authors]Zhou Zhiren is Professor of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Li Le is Doctoral Candidate of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