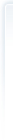
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3.05.0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1&ZD070)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新一届政府进行的大部制改革是前几次机构改革的延续,同时,它又意味着中国的机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大部制改革只有包蕴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题才称得上中国行政改革的中继站,否则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服务型政府建设既是一个长期目标,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方向。因为,人类社会正在发生一场后工业化运动,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它使既有的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政府模式显得不太适应。机构改革的深刻内涵应当是政府模式的重构,服务型政府建设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关键词]大部制;机构改革;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5-0007-04
2013年的两会后,新一届政府的行政改革被确认为“大部制”改革,或者说,“大部制”改革是新一届政府行政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就大部制改革而言,表现出与上一届政府行政改革工作的连续性,可以说舆论准备和操作方案的准备都已经进行多年,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而且,学术界也为之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和探讨,对大部制改革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也基本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性建议。因而,我们相信此次行政改革能够取得预期效果。2004年,中国政府为行政改革确立了一个总体目标,那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但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一个很长时期中,它都将是引领我国行政改革的总纲领,我们在行政改革过程中每一项措施的选择,都应当朝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前进一步。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在行政改革方面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必须是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行动,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总目标就是衡量行政改革的尺度,凡是有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行动,就是积极的,否则,就可能是走了弯路。
一、作为机构改革的“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标志着中国行政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它是1998年以来的机构改革的延续,依然属于机构改革的范畴;另一方面,在1998年以来的十多年机构改革的基础上,开始用“大部制”这个概念去表明机构改革的重心所在,从而使机构改革的切入点和工作重心都变得更加明确、内容更加清晰。所以,大部制改革是机构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的标志。可以预见,随着新一届政府的大部制改革达到预期目标后,机构改革这一主题下所要做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可以把政府行政改革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其他方面。除非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对政府结构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否则,可以不再把主要精力投向机构改革方面。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政府自身的行政改革一直是以机构改革为重心的,是通过机构改革去带动政府职能、管理方式以及行政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十六大召开前后,关于行政改革有了新的提法,那就是提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此,学术界曾一度将其解读为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机构”转向“体制”。然而,实践证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或者说,中国政府依然需要通过机构改革去带动体制的改变。这就是本届政府把大部制改革确立为行政改革重心的原因。但是,与此前的机构改革相比,大部制改革与体制改革的关系更为贴近,会直接地触动体制,会使行政体制改革感受到更大的压力,甚至会直接引发行政体制的多方面变革。所以,在大部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行政体制发生更大的变化。
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在1998年的机构改革中,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和理顺关系是合而为一的主题,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它们之间的区别而言,这三个方面是机构改革的三项任务,是不能混同的。但是,这三个方面又有着有机性的关联,任何一项目标的实现都可以使其他两项目标得到同时实现,反而任何一项改革的不到位,也都会使其他两项目标无法得到实现。就始于1998年的机构改革而言,这三项目标都基本实现了。但是,改革是一个行进的过程,在改革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出现新的问题,会积累起新的矛盾。所以,1998年的机构改革并不是机构改革的一个终极版本,必须持续地开展下去。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是不能触及也不允许触及的。这就是改革的性质所决定的,在每一个具体的时期,都只能实现属于这个时期的具体目标,如果改革的行动带有非现实的诗意内涵,就会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发现的问题也必须留待今天去加以解决。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1998年的机构改革和十六大之后直至新一届政府的改革之间,看到了某种连续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这几次机构改革之间的不同特征。
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机构改革并不是政府自身建设的终极目标,机构改革必须有一个超越自我的目标和明确的方向,而且这个方向应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贯穿于每一次具体的机构改革过程之中。事实上,在2004年,中国政府就确立起了这个方向,那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包蕴于机构改革行动之中的内在的灵魂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而答案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无论我们在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方面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取得了多么大的成绩,都必须沿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前行。我们的行政改革必须始终贯穿着走向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追求,须臾不可忘记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如果我们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仅仅关注机构的调整,忽视了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一主题,那么,就是目光短浅的做法,即使我们在一个时期中取得了机构改革的预期成就,但很快就会发现新的问题出现的,就会发现改了的东西还要改过来,就会陷入“折腾”的陷阱之中。
从机构改革到体制改革,再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模式,是一个层次迭进的主题系列,前者必须从属于后者。因而,在我们的行政改革路径的探索中,进行机构改革的时候,必须充分认识到将会对体制带来哪些变化,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当我们注意到体制方面的变革时,又必须看到它是否偏离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只有朝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前进,才意味着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
二、机构改革的现实与理想
克罗齐耶认为,“社会既不是柔软的面团,可供改革者任意揉捏塑形,也不是坚固的整体结构,必须用炸药将其炸开,而是处在运动过程之中的整体,其间运行着巨大的能量。假如我们可以如此看待社会的话,那么改革所提出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这样一个问题:使这类巨大的能量得以耗散,或更为准确地说,使这类能量不向消极的指向或保守的维度转化。” [1]改革者需要顺势而为,在某种意义上,需要认识清楚蕴含于社会之中的这种巨大能量的性质,并加以引导,使之服务于改革的目标。改革者不能凭着自己的兴趣和偏好行事,不能单凭自己的一厢情愿去确立改革的目标,即使自己对改革的期望是正确的,也需要根据客观情势去制定行动方案。总之,改革者决不能采取与社会中所蕴含的那种能量相背离的态度,如果那样的话,再好的改革愿望也会碰壁。就改革与革命不同而言,革命运动的爆发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伴随着社会失控的局面,而改革的过程则是可控的。对改革过程的控制决不是对社会的控制,相反,改革过程的可控制性恰恰是根源于对社会的正确引导,即把社会中所包含的巨大能量引导到某个方向,使这种能量逐渐地释放出来。
其实,对于积存于社会之中的能量,是可以进行抽象把握的,是可以从中发现要求社会走向某个方面的愿望的。如果能够把握这一点的话,也就能够形成较为清晰的改革目标了。所以,改革目标并不是改革者凭着主观愿望去制定的,而是社会期望和要求的反映。比如,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就不能把社会管理简单化为社会控制,因为我们的社会并不存在即将失序的危机,并不存在引爆革命和大规模动乱的矛盾,所存在的主要是对社会自主与自由的追求,是要求以更多的自我治理去矫正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呆板和僵化,试图打破的是因政府社会管理引发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问题。如果政府进一步强化社会控制的话,只能置自己与社会期望和要求相对抗的境地,其结果反而会使矛盾进一步加剧,使问题积累起来,以至于引发出意想不到的危机。以上访为例,在中国的上访人群中,肯定存在着一些无良之辈,但就上访行为而言,所表达的是对中国民主制度的信任,是对更高一级政府主持公平、正义的信赖。虽然会有人利用这一制度去谋取额外的利益,但这些人却不是站在反政府、反社会的立场上的,恰恰是用脚投了政府的赞成票。即使是出于某种不良的动机,但在表现上也必须被理解为投了赞成票和信任票。但是,我们是如何对待上访人群的,我们是对上访现象加以控制、阻止、杜绝还是把上访人群中所包含的能量转化为改革的资源?这显然是需要加以反思的。这些问题就是机构改革面对的现实,是大部制改革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我们决不能把大部制改革理解成政府机构的简单合并和归类,而是要通过机构改革使政府在解决当前社会中的那些棘手的、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方面体现出更多的优势。
在分析改革的原因时,克罗齐耶指出,“在政治、经济领域,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与机构之中,我们的管理体制依然建立在这样一种简单却威力强大的机制之上:级别种类的分割、诸种情境的分离以及技术的分割,使得社会性与职业性的屏障继续存在。此类机制阻碍了自由的交流和沟通,允许权威依然以疏离追他者及保守秘密的方式行使权力,其系统也更为坚固,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然而在当今,它却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可以用来提出要求与施加压力的途径越来越多,诸种社会屏障业已颠覆,但分割的技术与分割的局面未能有效地将其取代。体制尽管处在持续不断的危机之中,但是却依然存在,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未能建立起一个可替代的体制的原因所在。” [2]所以,行政改革是我们这个社会治理过程中须臾不能忽视的主题。但是,克罗齐耶所揭示的问题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以此为出发而制定改革的行动方案,可能是缺乏可操作性的,甚至是一种带有空想性质的方案。改革并不是要通过一次行动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改革只能是渐进的。因而,把行政改革分解为机构改革、体制改革,并对之作出有序的安排,才是可行的。同时,机构改革也需要分步实施。把中国政府历次机构改革的具体目标和行动方案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前进方向和以次递进的策略。可以说,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机构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入的递进过程,包含着一条走到新一届政府的大部制改革逻辑线索。这说明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一直坚持了现实性的原则。
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现实性的原则,在切实可行的每一个方案中去求得每一个小的进步,是保证改革持续推进的正确策略。但是,如果改革者缺乏理想的话,就会在陶醉于改革所取得的进步中失去目标和方向。克罗齐耶认为改革的重心是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他说,“不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无法改变社会结构,也就无法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然而要改变行政管理体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则是可能的,由此可以改变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结构的诸种条件。” [3]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的几百年间所采用过的政府改革策略都不能够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府改革经验,也是不可以照搬的。因为,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政府无法满足社会要求的问题,有一些是西方国家及其政府曾经经历过的,而更多的则是来源于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西方国家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遇到了一些共同的问题,并没有某种现成的西方经验可以借鉴。如果我们不予深究地把西方国家既有的经验搬过来的话,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现我们陷入到某种难以预料的泥潭之中。这是中国政府改革时代的现实,而基于这一点去谋划改革的时候,就会让改革的方案中包含着理想的成分。事实上,就中国的机构改革一直围绕着“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和“理顺关系”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而言,其实是包含着中国“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两个方面的内容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是包含着建构服务型政府模式的理想的。所以,包括大部制改革在内的全部机构改革都包含着改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内涵,机构改革无非是一场整体性社会变革的热身运动,当机构改革确立起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时,更是明确地宣示了通过政府的服务定位去改变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追求。如果说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把对社会进行统治的政府改造成通过对自身的管理而实现社会管理的政府,那么,我们的大部制改革所要实现的则是把现有的政府改造成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政府。在这一点上,理想与现实是统一的。
三、紧扣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题
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中说:“政府是我们使用的一种工具,一旦这个工具过时了,重新发明的过程就开始了。”[4]大部制改革,及至整个机构改革的过程,都不能称作是对政府的重新发明,而是一种幅度较大的调整。不过,我们在此过程中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我们现在拥有的政府模式是在工业化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虽然在近代以来的几个世纪中这个政府都有着无比优异的表现,但是,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它的不适应性暴露地越来越明显,把它说成过时了的工具决不过分。所以,我们必须基于后工业化进程中所显示出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去重新建构政府。如果“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和“理顺关系”的机构改革已经考虑到了当前社会中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的话,也会使我们的政府显示出高效、经济和公共服务得以改善的状况。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仅仅在机构方面进行调整甚至改革,是不可能让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构起来的政府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的要求的。
克罗齐耶在分析社会变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时指出:“一方面,行政管理体系将所有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都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如果不对这一体系进行改革,要对社会进行变革是极端困难的;另一方面,对行政管理体系进行变革,必然会遭遇艰难险阻,变革几乎无法触及这一体系本身。所有人都将自己的时间用于谴责这一体系的诸种弊端,但却从未获得任何成效。行政管理体系具有极为强大的内聚力,能够轻而易举地吸纳诸种变革并对其加以同化,而对其自身的功能运行机制,却未做出丝毫实质性的改革。”[5]克罗齐耶是基于西方的经验而作出这种判断的,认为政府即使举起了改革的旗帜,也不会改变自身作为一种阻碍社会变革的保守力量的性质。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政府是愿意通过改革自身而去适应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尽管如此,我们在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突出强调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依然是必要的。目前看来,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已经得到政府部门的广泛接受,而且全社会也都对服务型政府建设表示赞同。尽管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己的服务型政府标准,尽管政府也只是在口头上表示要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尽管要真正形成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氛围还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在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下,能够积少成多地积聚起行政改革的宝贵资源。而且,这些资源会成为推动行政改革的动力。
但是,在走向服务型政府的征程中出现一些怀疑甚至杂音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服务型政府理论直到今天还只能说是刚刚出现,与一切新生事物一样,这一理论健康的内核还显得极其弱小,它所面对的是近代以来经历过充分成长的管理型政府理论的话语霸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屈服于管理型政府的话语霸权而对服务型政府理论怀有敌意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也看到,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只是由于他们的思维被管理型政府话语所格式化而失去了对新生事物的识别能力,从而对“服务型政府”一词作出了误读,以为它是在管理型政府话语体系中生成的一个新名词。事实上,就学术界的情况看,对服务型政府的研究是存在着两种倾向的:第一,在将服务型政府定义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模式的时候,完全割断了它与管理型政府间的联系,使服务型政府成了脱离人类社会治理文明大道的一个怪胎。其实,服务型政府是在管理型政府难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新的要求的情况下提出的新的构想,就人类社会发展到任何一个高级阶段都必然包含着历史上曾有的生活内容而言,其社会治理也会将其历史发展中的积极成就加以全部继承。所以,服务型政府会包含着管理型政府甚至统治型政府所创造出的积极的治理文明成就。第二,是在缺乏模式意识的情况下把服务型政府与管理型政府混同起来,或者说,仅仅把“服务型政府”作为一个新的名词,用这个新的名词对管理型政府加以重新包装,在服务型政府的名义下去对管理型政府作出新的解释。在这种对服务型政府的解读中,如果说也存在着积极探索的话,那就是在服务型政府的名义下探索完善管理型政府的途径。与公开的怀疑和反对服务型政府研究的人相比,这两种倾向更具有危害性,特别是那些在服务型政府研究的名义下把服务型政府建设庸俗化为对公共服务的改善提出改进意见的做法,往往直接地对服务型政府研究造成方向性的误导。如果存在于学术界的这些问题作用于实践过程并被实践部门所接受的话,就会使机构改革的属性发生变化,从而丧失目标。
不过,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个构想本身就是非常积极的行动,更何况这一目标的提出是在对中国机构改革成果的总结基础上作出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政府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较大的四次机构改革后才寻找到了服务型政府这一目标。自从2004年提出了这一目标后,政府的行为方式、治理理念等各个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可以相信,新一届政府的大部制改革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具体举措,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要步骤和一个必经的阶段。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2][3][5][法]米歇尔·克罗齐耶.法令不能改变社会[M].张月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1.33.64-65.67-68.
Michel Crozier. Laws cannot Change the Society.Trans.by Zhang Yue.Shanghai: Truth & Wisdom Press,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7.p61,p33,pp64-65,pp67-68.
[4][美]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周敦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3.
Osborne,Gaebler.Reinventing Government: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Trans.by Zhou Dunren et al..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1996.p23.
(作者: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46)
Perfecting the Super-ministries System Reform on the Basis of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Zhang Kangzhi
[Abstract]The super-ministries system reform made by the newly government is a continuation of previous institutional reform, which also mean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However, unless these reforms are the theme of the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building, they cannot be regarded as the relay st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China. The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building is a long-term goal as well as the basic direction we must adhere to because the human society is undergoing a post-industrial movement and showing a high degree of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kes the existing model of government established under conditions of low complexity and low degree of uncertainty seem not adaptable.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should be the re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model,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must be the only right choice.
[Keywords]super-ministries system,institutional reform,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Author]Zhang Kangzhi is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