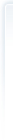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公民友好型政府预算报告模式研究”(编号:11YJA630137)
作者:王雍君,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财经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北京100081
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5.08.04
安全、正义与绩效:当代中国的行政治理改革与财政制度建构*
王 雍 君
[摘要]在本届政府致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确立行政治理改革的三个核心主题——行政安全、行政正义和行政绩效,在此基础上建构行政治理与现代财政制度之间的联结机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也更紧迫。本文的中心思想是:在公地范式和代理范式下致力推动走上正轨的现代财政制度建构,可为促进行政安全、正义和绩效,进而为提高行政治理改革的成功概率提供最佳保障和理想切入点。
[关键词] 行政治理;现代财政制度;安全;正义;绩效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8-0023-07
一、引言
行政部门是政府治理的心脏。[1]倘若没有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国家仍然能够实施治理;但若没有行政部门,国家治理便断无可能。虽然如此重要,旨在改进和强化治理能力的行政改革却鲜有成功,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
许多文献解释了行政改革效果不彰、失败案例远多于成功案例的原因,但大多不能令人满意。这些文献既未从治理视角看待公共行政,从而难以形成一个包容性框架来锁定和协调安全、正义和绩效这三组既互补又具潜在冲突的治理价值;也未能在公共行政与公共财政之间建立起清晰联系,从而缺失了以现代财政制度建构推进行政良治的视角。作为两门显学,行政学和财政学一直在两个平行、少有交叉的领域得到发展,彼此的主流话语都很少呈现两者间的关联,尽管两者的真实关系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那样清晰:公共行政和公共财政都是多维的,而且彼此都是对方的一个关键维度。缺乏对关联机制的认知使我们很难设问:在指向安全、正义和绩效的行政治理改革中,现代财政制度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理想且可行的路径建构是怎样的?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回应这两个攸关行政与财政改革成败的重大问题。第一部分从财政视角确立行政治理的概念框架:以财政分离和民主授权作为逻辑起点,将行政治理看作广阔经济社会背景下控制公地悲剧和代理问题及其负面后果的方法。第二和第三部分分别在公地范式和代理范式下,界定行政安全、正义和绩效的含义并寻求对应的财政机制建构。最后,结语部分鉴别了中国行政治理改革的核心命题,即通过财政制度的现代性建构促成行政改革取向的转型,将组织取向深度整合到注重功能取向的改革模式中。
二、财政制度现代性视角下的行政安全、正义和绩效
现代行政部门拥有广泛权力、控制着庞大资源并肩负重大的治理责任,得以在政府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见图1)。在权力和资源清单中,没有任何一个比财政权力和财政资源来得更加紧要了。

图1 2003-2013年国有资产规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财政支出总规模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2004-2014年《中国会计年鉴》和《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国有资产规模=全国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总额+行政单位国有资资产总额+事业单位国有资资产总额。
在此视角下,行政治理可视为行政部门运用财政资源和财政权力促进治理目标的行动,包括行动的方法与过程。行政治理的关键特征就是行动,而一切行动都预设了对某种善恶或好坏的价值判断——本文将其鉴别为安全、正义和绩效三组价值,它们并不能从治理概念本身推论出来,但每个都表达了当代中国行政治理亟需应对的关键挑战,这些挑战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
对行政治理挑战的妥善回应,不仅要求锁定安全、正义和绩效作为良治的关键目标,还要求为每个目标指明所依赖的条件或路径。然而,主流文献几乎未能意识到,正是财政制度的现代性建构提供了指向行政善治的最优路径。为理解这一点,有必要简要回溯理解财政制度现代性起源的两个范式:公地(共同财产)范式和(委托)代理范式。
财政制度系一套管理财政资源与财政权力的原则、规则、程序和实施机制的集合,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安排。随着人类开启民主与法治进程,君主财产与国家财产分道扬镳,财政资源再也不是君主的私人财产,而是民有、民享、民治的共同财产。本文将这一历史进程称为财政分离,它带来了与管理君主财产全然不同的崭新态度、观念和制度安排,成为现代财政制度建构——现代性建构——的第一个逻辑(也是历史)起点。现代公共预算制度正是财政分离的直接结果,行政治理的工具、方式和样貌也因此发生根本变化。
财政分离的本质是国家将私人财产的一部分强制地转换为共同财产,以增进广泛的公共利益。共同财产的创设虽然绝对必要,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和持续的副作用,酿成所谓的公地悲剧:每个人都去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走向毁灭就是这块公地的宿命;公共用地的自由会给所有人带来灾难。[2]悲剧的根源恰在于共同财产与私人财产截然不同的产权特性:人人都可得到、人人又都无法得到。正如斯科特·高登所说,“人人所有的财产其实就是每个人都得不到的财产;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财产不会有任何人珍惜”。[3]早在此前一个多世纪,亚瑟·杨格就精确表达了财产权的魔力:给一个人一块荒凉的砂砾地让他拥有,他会将其变成一座花园;给他9年时间花园的租借权,他又会将其变成一块沙漠。[4]
一般地讲,私人财产被转换为共同财产的规模越大、方式越恶劣,公地悲剧越严重。给定共同财产的规模,共同财产的错误配置和使用也会加剧公地悲剧。经济学家经常使用超额负担(excess burden)、有时使用公共资金的机会成本(OCPF)来表达,包括征税带来的微观经济的无谓损失、行政成本、腐败、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其他与公共支出相关的社会交易成本,比如财政资源的错误配置和使用造成的成本;在西方国家,其数据约高达公共支出规模的1.2-1.3倍。[5]考虑到税制缺陷更明显等因素,中国很可能更高。
这些温和术语不足以表达共同财产(公地)的悲剧本质和全部后果,即共同财产的创设、分配、使用和管理蕴含极高的社会交易成本。回溯人类专制统治的历史不难得出结论:专制政体使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更多的是它妨碍人民发展生产,而不是它夺走人民的生产成果;它使财源枯竭,却始终重视既得的财产;自由与此相反,它生产出来的财富比它所毁掉的多千百倍,人民的资源的增长总是快于税负的增长。[6]在此视角下,公地悲剧不仅指所有人都可得到的东西最终难逃遭人肆意破坏的命运,而且包括对社会成员创造财富潜力的压制,由此导致的损失比前者很可能大得多。
公地范式提供了现代性建构的第一个不可逾越的逻辑起点。同样不可逾越的还有伴随民主授权安排而来的代理范式。共同财产是一回事,管理共同财产是另外一回事。在规模稍大的共同体中,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全体人民在保留共同财产的集体所有权的同时,管理共同财产的权力必须被授予人数相对较少、具有专业特长和技能的代理人——行政部门正是其中最重要的角色。在民主治理的背景下,代理人创设和管理共同财产需得到代表人民的立法机关正式和明确的授权。立法机关通过审查和批准法律(包括作为法律文件的年度预算),将获取(创设)、配置和使用共同财产的权力授予政府,成为现代社会政府合法性基础的首要来源,也是财政制度现代性的第二个最重要的起点和标志。(注:关于统治者权力正当性终极来源的前现代观念与现代观念截然不同——诉诸人类经验和科学无法证实或证伪的“神”、“天”或造物主。一般地讲,任何将法理学建立在造物主语言或自然造化之上的尝试终将失败,因为造物主或自然从来不曾以人类可听闻或可理解的声音发言。参见:艾伦.德肖维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黄煜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授权安排对约束和引导行政治理与财政政策的运作至关紧要。政府只能依据法定和适时的授权采取财政行动,这是善治诸原则中最基本的一项原则。[7]
然而,正如共同财产安排(国家财产与君主财产的分离)带来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公地悲剧)一样,授权安排也产生了另一类副作用:代理问题。经济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人类预见未来的能力天然不足,意味着授权不可能(也无必要)做到巨细无遗,从而让代理人获得了自由裁量的很大空间。被授予或未被授予的权力越大,自由裁量的余地越大,代理人滥用或误用权力榨取租金的机会越大。人性的局限性和人类对历史上不绝如屡的“权力恶行”的集体记忆,都提醒我们对代理人滥用权力推进狭隘利益时刻保持警觉,迫使我们设计有效的治理安排来防范恶行的再度发生,受托责任(accountability)就是其中的关键元素。
当代的行政治理恰好就卡在财政制度现代性建构无可回避的两类困境中。首要的是共同财产安排带来的公地悲剧,其次是授权安排带来的代理问题。历史经验和现实告诉人们,没有确立共同财产和授权安排的财政世界原初风险极大,但确立这两类安排的财政世界依然是个具有附带风险的世界。我们甚至不知道附带风险是否比原初风险更大、更恶劣,除非能够为控制这些附带风险指明目标与方向,同时指明该如何到达那儿。这就要求将着眼组织整合的行政改革,推向更高的功能层次。
中国历次行政改革之所以效果不彰,关键原因正在于痴迷于组织层面机构分合的同时,对着眼于功能层面的行政治理及其价值诉求缺乏清晰的概念框架和路径建构。主流文献不仅没能锁定当代行政改革的三个功能性主题——行政安全、正义和绩效——及其相互关系,也未清晰认识到财政制度的现代性建构才能为其提供最佳保障。直到今天,无论在行政学还是在财政学中,公共行政与公共财政之间原本存在的关联机制依然模糊不清。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改革和财政改革很难走上正轨,失败的风险变得很高。
对于走上正轨的行政改革和财政改革而言,安全、正义和绩效绝不是偶然的陪衬,而是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和主题,需要倾注比过去多得多的时间与精力,以使组织取向的行政改革和财政制度现代性建构困境发生逆转:在确保组织取向服从于功能取向的行政治理改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控制公地悲剧和代理问题负面后果。同等重要的还有厘清三大主题间的关系,尽管本文的重点不在这里。除了以某种安全、正义和绩效观念为基础外,当代行政治理还必须为这些信仰给出强有力的理由或论证,避免以信仰取代理性或真理的错误倾向。理性和真理都要求我们根据正确的标准——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正确的东西——来做出判断。最重要的是,必须在起点上就保证判断标准的正确性。要想解决广阔经济社会背景下的治理难题,就要回到招致问题的根源上去,立足于业已公认的事实这一低且稳定的基础之上。与所有事业一样,从最初的地方起步总是最好的。
就行政治理而言,最初的地方就是财政制度现代性建构的两个逻辑(也是历史)起点:首先是由共同财产安排及其衍生的公地悲剧,其次是授权安排和作为其副产品的代理问题。(注:正是共同财产和民主授权安排为财政制度的现代性打下了最为深刻的烙印。源自国家财产与君主财产分离的共同财产安排,破坏了前现代的国家财产即君主财产的观念体系和制度安排;授权安排和作为其直接产物的委托代理关系,则破坏了统治者的合法权力取自上帝(天、神、自然或世袭传承)、统治者无须与臣民分享权力、臣民必须顺从只有统治者才能制定的法律且无权参与公共事物的前现代观念和制度体系。在此意义上,公地范式和代理范式得以成为财政制度现代性建构的量佳分析框架,也是在后者与行政治理之间建立联结机制的理想路径。)缺失了公地范式和代理范式的建构视角,行政治理将变异为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不成其为真正的治理。借助公地范式和代理范式为行政治理准备的基本框架——基本的概念与范畴,我们才能着手正确思考行政治理,包括行政改革的核心的命题和关键议程,以及重构公共行政和公共财政之间原本存在但久已失语的内在联系。
遵循这两个范式并不意味着可以得到全部正确的答案,但范式本身使我们以无与伦比的清晰和洞察力提出问题成为可能:为使行政治理被塑造得足以抵抗公地悲剧和代理困境,确保行政治理锁定安全、正义和绩效主题,并将它们还原和安置到财政制度现代性建构的中心深处非常重要。但这一努力不应让我们模糊两个范式间的基本差异。特定主题下的行政治理的不同风格、样貌和路径,也可在不同范式下呈现出来,共同拼接成当代行政治理的完整画面,并标示出彼岸所在以及我们该怎样从此岸到达彼岸。
今天,安全、正义和绩效依然冲击着财政制度的现代性建构,要求我们在两个相关但不同的范式下作出回应。任何单一视角都过于狭隘,并且不能保证行政善治的出现。大致来说,公地范式通过聚集资源话语、代理范式通过聚集权力话语进行建构;前者着眼于约束和引导作为共同财产的财政资源的运作,后者着眼于约束和引导行政部门权力的运作。两套话语的结合使得行政治理和财政制度现代性建构相得益彰,轮廓和路径变得清晰可辨。此外,需要被建构的不只是范式本身,更有特定范式所指引的相互联结并可切实运转的财政机制。毕竟,治理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延伸,而政治要解决的是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必须扎根现实,具有可行性。[8]
三、回应行政治理挑战的财政建构:公地范式
一旦置于公地范式下,当代行政治理面对的根本挑战就是有效控制由利维坦创设的公地悲剧及其负面后果,并联结相关的财政机制:指向行政安全的财政控制,指向行政正义的预算竞争机制,以及指向行政绩效的结果管理和财政融资机制。这些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分别对应着现代预算制度的三级结构:宏观层次的总额预算、中观层次的配置预算和微观层次的运营预算。(注:详细讨论参见艾伦.希克:《当代公共支出管理方法》,王卫星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首要的是财政控制。公地悲剧的严重性与规模相关:给定社会财产总量,被强制转换为共同财产的部分越多,暴露于公地(共用资源池)风险中的部分也越多,共同财产本身越是处于不安全状态;私人财产和一个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也是如此。因此,解决公地难题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正确的答案——关键在于确定所有权:如果必要就确定集体产权,如果可能则确定私有产权。[9]
循此思路,财政控制机制就成为行政安全的关键屏障,包括旨在限制财政总额的各种宏观财政规则、中观层次的预算限额、微观层次的条目(line-item)基础的投入控制,后者以大量按对象、用途设置的预算科目限定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每笔支出都被预设特定标准(比如资产配置标准和人员编制),不同科目间的资源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资金结余通常必须上缴。这些似小实大的财政控制机制,对于防范过度开支(以及赤字和债务膨胀)、保障共同财产安全至关紧要。
鉴于逃避约束的动机和花招无处不在,为使财政控制机制真正有效,监督(包括定期检查与审计)和透明度机制需要一并建立和充分实施,这些支持性机制需要覆盖全部公共资金(包括债务和或有事负债)、公共资产和由其支持的活动。理想情况下,各种准财政活动(quasi-fiscal activities),包括国有金融机构、非金融国有企业和其他形式的准财政活动,亦应纳入控制范围并建立起至少不低于类似正常预算程序的治理安排,并遵循善治的基本原则:受托责任、透明度、预见性和参与。[10](注:准财政活动指那些起着与财政工具类似作用、但没有直接资金流的活动。在政府参与的各种准财政活动中,税收支出、政府贷款(政策性贷款)和贷款担保最为典型,国有金融和非金融企业也是准财政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财政控制的逻辑基础根植于限制预算极大化(官僚行为的典型特征)和防范资源错配的需要。放任这类行为将破坏财政可持续性、招致资源误用,诱发和加剧公地悲剧:置公共财产、私人财产和财富创造活动于高风险状态。防范这种资源风险正是公地范式下行政安全机制建构的根本目的。没有有效的财政控制,就不会有真正的行政安全,但传统的行政改革大多忽视了这些机制的特殊重要性。
除了风险因素外,公地悲剧还取决于创设和管理共同财产的正义性质。正义概念比多数人懂得的还要复杂得多,但即使是普通人,也可能对什么是正义有着广泛的底线共识:正义几乎总是与利益获取方式相联系,偷盗或巧取豪夺行为可立即被判定为非正义,因为其本质是以丛林法则等非正当方式获得利益。推论起来,以正义方式获取资源的基本要求就是互惠。对私人部门而言,互惠根植于生产和交换活动中;对公共组织而言,互惠的核心则是社会偏好和成本,任何偏离该方式的资源获取方式都传递出不义的信号。
基于公民财政偏好与成本的资源获取与占用,高度依赖于某种适宜的预算竞争机制,该机制保证预算中优先采纳那些能以合理成本满足公众偏好的政策。在实务上,预算竞争的核心是一套将预算与政策直接结起来的程序,其中最具应用前景的莫过于中期支出框架(MTEF)和部门战略计划。立法机关对预算的严谨和现实的审查,对于引导良性预算竞争至关紧要。同样不可或缺的还有自下而上的受托责任(对下负责)、公民偏好充分反映在预算中以及广泛的公民参与。没有这些基本条件,本应存在于正常预算过程的预算竞争机制要么不能被激活,要么会滑向破坏性竞争的深渊。
只要基于财政偏好和成本的预算竞争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压倒组织驱动和收入驱动的预算模式,公地范式下的行政正义便可得到保障。财政偏好概念传递了公共财政的一个基本问题:如何让我们的政府提供的,恰好也是公民所需要的,并且公共支出排序恰好反映公民的意愿。开发公民真实财政偏好的揭示机制,可为推动以社会为基础的改革和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方式,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然而,这方面一直存在令人敬畏的挑战。作为替代,组织驱动模式并不适当,因为它将组织本身作为资源分配决策的基础单元,采用盛行的基数法、法定支出、部门专款(基金)和内部交易(互投赞成票)等方式,固化和强化权力在资源竞争中的优势地位,造成普遍的预算僵化并使资源分配的正义基础不断流失。过度集权的政府间财政安排的后果与此类似。由于在方案设计和实施时几乎未能将预算竞争机制考虑进去,多数行政改革在正义主题上少有作为。
对公地悲剧的完整控制还需诉诸引导结果(results)的财政机制,以及旨在使公共资金机会成本(OCPF)最小化的财政融资机制及其组合。这是资源话语下行政绩效的两个关键方面。传统的绩效概念过于狭隘,只是关注公共支出(资源)的质量——通常表达为3E,即理想成果的三个层次:经济性、效率和有效性(effectiveness)。为确保有效,结果管理机制应以某种方式嵌入公共预算过程的各个阶段。
结果绩效虽然在新公共管理中得到特别强调,但却忽视了行政治理的另一个绩效要素:为行政部门庞大的支出和资产占用进行的财政融资,无论采用怎样的方式——税收、非税收入、债务、互惠融资(比如道路使用费)和非互惠融资(比如所得税和罚没收入),通常具有很高的机会成本(本质是社会交易成本)。因此,有必要为行政绩效建立更加完整的概念框架,使其能包容结果管理机制和财政融资机制,两者都包括绩效评价和绩效驱动两个基本维度。无论如何,绩效是一个要求严格的测试:当一个政府不能完成这个测试时,其合法性和能力就要受到质疑。[11]
四、代理范式下的行政治理改革与财政建构
当代行政部门不仅掌管着庞大的资源,也拥有和行使着巨大的权力。为防范和抗衡滥用权力的自然倾向,人民或其代表在通过宪法和法律授予政府权力的同时,也一并将责任授予政府,以约束和引导政府就权力来源、配置和使用担负起真正的责任。在许多国家,行政治理的脆弱性与受托责任安排的脆弱性(行政部门有权无责、责任模糊和问责无力)紧密相连、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些国家,当代行政治理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构、改进和强化外部与内部的受托责任安排,以促进基本的行政安全、正义和绩效,财政制度现代性建构的首要任务也在于此,而建构路径主要取决于治理主题及其含义。
代理范式下的行政安全可定义为行政权力偏离合理边界而侵蚀其他(特别是立法机关)权力、损害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可能性。权力边界难题一直纠结着当代的行政治理。宪法和法律为行政界定了行政权力的边界,但行政部门在边界外乱作为(越位)和边界内不作为(缺位)的现象十分普遍,两者都具有危害性,旨在保障行政权力安全的五种财政底线机制——财政授权、财政分权、财权集中、预算会计和公款监控——因而变得特别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财政权力在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间的适当平衡,以防范行政强势、立法弱势对公共利益构成种种潜在或现实的威胁。隐含的逻辑是:没有财政权力的安全就谈不上行政权力的安全。
首要的是财政授权:在公民未通过其代表例如立法机关正式、明确和适时授权的情况下,政府行政部门既不能从公民那里拿走任何资金,也不能通过预算实施任何开支。[12]在实务上,这意味着行政部门不得自行创设针对公民和企业的财政义务,包括各种形式的预算外资金;这些义务只能受制于法律,而法律必须得到立法机关的严格审查和正式批准,年度预算亦如此。财政授权安排对行政权力构成各种规制,包括税法规制、预算规制(budgetary regulation)以及相关部门法律(如教育法和农业法)和部门专款形式的规制。为使财政规制真正有效,严格区分财务法案和非财务法案,特别是确保预算规制在各种财政规制中的最高地位十分重要。一般地讲,如果预算缺少规制公共财政的能力,那将不可能会有一个强大的政府。[13]
同等重要的还有财政授权的质量,以及立法机关约束行政部门遵循规制和在授权框架内实施治理的能力,这进一步要求立法机关(人大代表)有足够的代表性、专业化和职业化,并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完整且牢固的程序对公共预算与财务报告进行严谨细致的审查,预算会计(budgetary accounting)和财政审计亦则有必要作为立法机关的左臂右膀发挥作用。
由于财政授权大致界定了行政治理的边界,财政授权的范围、内容、详细程度、次序、方式、时效性和相关的监管机制,在立法机关审查预算时尤其需要被精心考虑,并需得到财务合规性控制(内部控制的核心)流程的紧密衔接,该流程覆盖公共资金循环的七个关键控制节点:财政授权、支出承诺、核实交付、会计审核、支付令签发、款项支付和付款后的审计。为确保预算授权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公款的动用须处于立法机关的有效(逐笔、全程和实时)监控之下。为此,财务合规性控制流程须覆盖法定控制和行政控制两个阶段,前者由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年度预算亦为法律)控制行政部门的资源获取与占用,后者由行政部门建立衔接法律或预算授权的内部控制机制。
财政授权(核心是预算授权)为公款的来源、分配和使用提供了最高规制,但如果不能与公款的有效监控相结合,极易变异为某种数字游戏。行政部门有能力(更有动机)制造数字以表明其所作所为与法定财政授权相一致,而真实世界中的公款来源、分配和使用很可能与财政授权大相径庭。这种表面遵循、实则背离授权安排以高度隐蔽的方式瓦解了授权安排的基石——现金基础的财政授权,从而置纳税人的钱袋子于高风险中。中国现行财政授权机制的这一重大缺陷,可以通过发展两种关键的救济机制予以矫正:旨在逐笔、全程和实时追踪公款流动的真正意义上的预算会计(budgetary accounting),以及财政部门和央行国库对政府现金流量与余额的定期报告。(注:详细内容参见王雍君“中国国库体制改革与防火墙建设”,载《金融研究》2012年第7期。)
防范代理人滥用权力还有赖于有效的政府间财政分权安排。过度集权即便有助于保障某种概念的国家利益,也将对地方利益——公共利益的极为重要的形式——构成侵害,尤其是在中国的多级政府体制、地方政府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中扮演主角的背景下。然而,财政分权只是在财权横向集中时才可能真正有效:管理财政总额以及功能、组织、经济甚至规划(programs)层资源分配的权力,集中于负责授权和监督的核心部门——尤指立法机关、政府高层和财政部门,而不应分散于各个支出部门。支出部门的适当角色是在其职责内制定政策、建立最低服务标准和监督标准的落实,而非垄断和控制财政资源。此外,行政部门的决策制定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须适当分离,置于同一部门将冒权力滥用的很高风险。现行体制下的这些明显软肋,很少在行政改革和财政改革中话语中得到表达,更不用说得到足够重视了。
现在转入指向行政正义的财政机制建构的讨论。在代理范式表述的权力话语体系下,行政正义可界定为行政权力来源、分配和使用对法治正义——涵盖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严格遵从。实质正义要求目的正当性测试以及目的-手段间的一致性测试。征税、开支、举债等财政权力只是服务于清晰定义的公共利益时,才应被视为目的正当;只有所采用的手段或方法为该目的所绝对必需,才应被视为手段与目的相一致。据此,公共预算必须清晰有力地表述每笔公共支出的特定目的,并充分说明所采用的手段与该目的相符。这些测试也适用于非财政权力——比如行政规制或许可的权力。在中国等许多国家,不断膨胀的规制国家(regulatory state)已经成为妨碍良治的主要标志之一,而行政集权本身就包含了规制国家的萌芽。[13]
与权力来源相比,权力分配的正义性建构更为复杂。除了目的正当和目的-手段间的一致外,分配正义还要求依据宪法与法律界定当事人的适当角色和责任,并据此分配相应的权力。如果权力分配破坏或弱化了与角色和责任的对称性,即可被判定为非正义。以此视之,实质性分配正义取向的行政改革和财政机制建构,焦点在于梳理和矫正财政权力的分配对角色和责任的偏离,包括由来已久的人大有责无权和行政有权无责,以及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不对称。另一方面,如果目标是促进权力使用的实质正义,那么,改革努力应转移到其他方向上,焦点在于对抗腐败所需的财政机制建构,以防范和惩罚权力寻租。
旨在促进行政安全和正义的财政建构也可能与指向行政绩效的财政建构相冲突,因而需要寻求不同路径。现行社会中,权力行使的关键是官僚组织,主要功用在于将权力转换为行政决策,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和棘手的治理问题。与公地范式下的资源绩效观不同,代理范式下的权力绩效观将行政绩效看作行政决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的质量和效率。
与西方国家相比,相对于立法机关而言,中国的行政部门在行政决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主导作用更为突出,决策的速度或效率似乎也略胜一筹,但经验证据表明行政决策的质量相差甚远,财政决策尤其明显:税收、非税收入、政府性债务、公共支出、补贴(大量分发现金)、转移支付(尤指专项转移支付)、政府采购、资本项目和政府现金管理的种种漏洞,以及准财政活动治理安排的种种脆弱性,显示行政决策的制订和执行质量远不能令人满意。此外,如果区分短期效率和中长期效率,中国行政决策体制也可能并无优势可言。
为此,财政机制的建构应着眼于提升行政决策的质量和中长期效率,重点是促进政府职能合理化、决策贴近性、专款合理化、决策机制内化于预算过程、组织整合以及决策过程的专业理性。(注:财政职能合理化关注公共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只有至少在原则上能够证明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才是政府职能的合理范围。专款合理化旨在清除过度碎片化的专项转移支付(针对公民、企业和下级),将其限度为具有广泛外部影响(比如环境保护和基础研究)的事项。决策机制内化于预算过程旨在形成“政策引导预算、预算约束政策”的良性预算程序,消除决策机制与预算程序的严重脱节。组织整合要求行政决策的适当集中(减少机构数量)、避免决策权过度分散导致领导力弱化和决策僵局。决策贴近性指凡是可能,决策应尽可能由最贴近受这些决策影响的层级或单元制定,而不是由局外人代行决策,以充分利用地方知识和信息。专业理性的三个基本要素是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和组织(分工与协调)能力。所有这些都深度影响决策质量和效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角色需要和责任需要重新界定,纵向集权的部门式决策决不可取代或压制地方的自主决策,规模庞大且过度碎片化的专款和法定支出体制亟需深度改革,大而不当的行政机构应以最有利于决策质量和回应性的方式进行整合,依赖“文山会海”与公章驱动(过度行政规制的标识)的行政治理模式宜尽快转向预算(程序与报告)中心的治理模式,旨在充分利用分散信息和知识的公民参与机制亦须致力发展。行政部门的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亦须尽快实现内外开放。特别重要的还有创设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允许和鼓励对公共政策成败得失的客观评估,以及建构相应的政策问责和救济机制。没有这些方面的足够努力,资源充裕的行政部门很可能同时也是决策上的低能儿。
五、结语:行政改革的核心命题与财政路径建构
美丽的理论能以最简洁的方式统一最大范围的现象。[14]然而,无论在公共行政还是公共财政领域,主流话语都缺失了“指南针”,即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清晰理解两者紧密关联且相互依赖的一般分析框架,这使得对未来的任何重大规划或改革都难以达成预期目标。作为回应,本文尝试融合公地范式的资源话语和代理范式的权力话语来建构两者间的联结,两者均可将行政话语贴切地包裹在财政话语中,反过来也是如此。
只要置于公地范式和代理范式下,当代中国的行政治理和财政制度建构都可看作对抗两类集体行动困境——公地悲剧和代理问题——的方法和过程。作为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侧面,两者具有共同的目标指向:安全、正义和绩效,它们在不同范式下具有不同含义,财政路径也有所不同。
其中,公地范式下的行政安全要求有效的财政控制,行政正义要求适当的预算竞争(核心是中期财政规划和部门战略计划)以引导资源基于财政偏好和成本的流动,行政绩效则指向融入预算过程的结果管理机制,以及旨在控制公共资金机会成本(OCPF)的财政融资机制。代理范式下,行政安全依赖于旨在防范权力滥用的以财政授权为核心的一组底线机制,以及财政权力在立法机关与行政部门间的适当平衡;行政正义依赖于旨在增进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财政建构;行政绩效则与旨在提升决策质量和效率的财政机制相联,特别是财政成本-收益分析(政府职能合理化的技术基础)、决策机制内化于预算过程以及支出政策评估与矫正机制。每个路径都有其特定含义,并超越了偏重组织整合的行政(机构)改革模式。当代中国行政改革最核心的命题,就是将组织取向的改革模式深度整合到功能取向的改革模式中,即锁定行政安全、正义和绩效,并致力于通过现代财政制度建构来最优地达成这些功能。
[参考文献]
[1][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第五版)[M].张成福等校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
[2] Hard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968(162).
[3] Gordon,H.S.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4(62).
[4] Brubaker,E. Property,Rights in the Defence of Nature. Earthscan,London,1995.
[5] Jerome.M, Gabriele.P: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Public Funds: Concepts and Issues.Public Budgeting & Finance, Fall 2013, Volume 33, Number 3.
[6][美]乔恩.埃尔斯特.宪法选择的后果:对托克维尔的反思[A].载Jon Elster and Rune Slagstad(埃尔斯特,斯莱格斯塔德).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C].潘勤,谢鹏程译.三联书店,1997.81-102.
[7] [10] [12] Salvatore Schiavo-campo. The Budget and Its Coverage. Edited By Anwar Shar. Budgeting and budgetary institutions,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2007.p84,p54,p16.
[8] 钱满素:自由的阶梯:美国文明札记[M].北京:人民东方出版社,2014.298.
[9] [13] [英]马特·里德利.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M].呈礼敬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209,229.
[11]Schick,Allen. The Performance State: Reflection o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but Whose Implementation Has Not. Oecd Joutnal on Budgeting,Volume 3,No. 2: 2003.
[13] Schick,Allen. Does Budgeting Have a Future? Oecd Joutnal on Budgeting. Vol. 2, No. 2. 2002.
[14] [加]戴维·欧瑞尔:科学之美:从大爆炸到数字时代[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Security, Justice and Performance: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Reform
and Fiscal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Wang Yongjun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ability by central government, three core themes of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reform can be established, which include administrative security, administrative justice and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se core themes, constructing a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and modern fiscal institution is more important and urgent than ever. The central idea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to push modern financial institution back on track in commons pool and agent paradigm can provide the best protection and ideal entry point to promote the administrative security, administrative justice and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and to increase the success probability for administration reform.
[Keywords]administration governance reform, modern fiscal institution, security, justice, performance
[Author]Wang Yongjun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