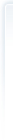
作者:戴维·H·罗森布鲁姆(David H. Rosenbloom),美利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海伦娜·K·芮妮(Helena K. Rene),美利坚大学美利坚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项目发展顾问。译者:叶杰,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730000
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5.08.25
认真对待当代公共行政中的行政法*
戴维·H·罗森布鲁姆 海伦娜·K·芮妮 叶杰译
[摘要]人们普遍认为,公共行政综合吸收了来自管理、政治/政策和法律的观点。然而,法律的观点并不被当代公共行政文献所重视,也被很多公认权威的美国公共行政硕士课程所忽视。行政法是规范公共行政决策和行为的法律体系,成熟的公共管理者必须在行政法的框架下并按照行政法的要求从事管理活动。本文阐释了行政法的内涵及其重要性,并用实例说明了美国行政法折射出的价值取向。本文的关注点在于规章制定、行政判定、行政执法、透明性以及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等五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规章制定;规章裁定;透明度;司法审查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8-0144-10
人们普遍认为,当代公共行政包含了管理、政治/政策和法律方面的问题。[1]然而,在该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文献中,法律却常常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目前,在全美高等院校公共事务和管理协会认证的大约60%的院校,学生可以在无需学习任何法律类课程的前提下就获得公共行政硕士学位。[2]“合法性”在公共行政价值中仅列第21位,远落后于诚实、人道、社会正义、公正以及效率和问责等价值取向。[3]针对MPA卓越教育,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特别工作组于2008年就已指出,“MPA学位教育的核心使命是提升学员的能力,使其能明智、有效与合法[4]地行使公共权力”。即便如此,行政法还是没有得到公共行政学界的普遍重视。如果要使公共行政理论、研究、教学与公共行政实践以及全球数十亿人的日常生活持续相关,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认真对待行政法。
一、行政法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行政法是面向公共行政的监管性法律。[5]它包括以下组成部分:宪法条款、判例法、成文法、行政命令和其它官方指令,这些法规用以监管行政机构在决策、裁定、执法、透明度、外包、利益相关者和其它外部参与、公私伙伴关系、合作治理等问题上的程序,也用以对法院、议会、总统、首相、州长以及直接对他(她)们负责的高级行政官员和行政单位所进行的审查。行政机构做什么、怎么做、为何做及其行为对内外部审查的服从度和透明性等,都属于行政法对行政机构的监管范围。虽然行政法也追求环境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等公共价值,但就其本身的定位而言,行政法主要是程序性的。从定义上讲,“行政法”这一术语是否涵盖具有法律效力的部门法规,比如,美国环保局关于洁净空气和水质的规定是否属于行政法,这类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各政治体系对该法规的认识。
在很多像美国这样行政法体系十分复杂的国家,如果不了解、不关注行政法,公共管理者就不可能有效管理员工、预算、部门,也很难做出高效的决策,更不能实现机构的使命。实际上,由于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政府和公共行政的极端重要性,行政法已作为一个词条进入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出版的《生命支持系统百科全书》。[6]
无论如何定义,行政法的概念、内容和边界仍可能不够精确,甚至有些难以名状。因此,通过一些例子也许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行政法。美国联邦的行政法体系包括以下内容:
1. 信息自由、公开会议,以及其它透明条款,其目标是向公众和媒体公开联邦行政决策和其它行政行为。
2. 面向咨询委员会的法规,这些委员会由代表性利益相关者组成,这些利益相关者将积极参与行政机构的议程设定、政策方案和执行方案之中。
3. 保护隐私的法规,此类法规的目标在于保护个人隐私免遭行政机构的无端侵犯,在于确保未经当事人允许的个人信息不被随意披露。
4. 公开会议法,该法要求针对特定问题的管理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举办相应的公共论坛,并按照规定向媒体和其它相关群体提供有关会议记录。
5. 要求行政机构在决策和制定政策、规则时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的法规,这些利益包括小企业和小团体的利益、环境可持续和环境正义、减少由政府引起的对公民的文书负担、家庭竞争力和家庭自治、较高的成本收益比、充满活力的联邦体制等。
6. 针对裁定和非诉讼争议解决机制的程序。
7. 协商式立法(“协商行政立法”,协商规章制定)等各类规章制定的程序。
8. 制定过程中需要采取同行评审和可重复性研究的规章。
9. 制定战略规划、绩效计划、绩效报告和绩效评估时的程序性要求。
10. 制定规则和通讯交流时行政机构必须使用通俗性英语的规定。
11. 强制实施产品召回等规章制度的程序性要求。
12. 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议会审查和总统复议的法规。
13. 有关举报者保护和联邦雇员人力资源的法规。
从上述目录不难看出,公共行政人员致力于三种政府职能:立法(通过规章制定等方式创设规章制度)、执行(实施与强制)和司法。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管理既不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功能,也不是公共行政的全部。公共行政的内涵与范围要比管理更多——而像对待管理一样管控好这些“更多”的内容就是行政法的主题。
从更为广泛的系统观点看,行政法有助于解决现代大政府引发的各类重大问题。这些大政府对普遍影响公众日常生活的各种情况和活动都要负起责任。公法和公共政策要处理的对象和领域包括:食品、劳动场所、交通运输、消费品、药物、医疗以及大量科技与化学物品的安全问题;经济绩效、经济行为和经济生活;教育;环境质量与可持续发展;国家安全;犯罪和反社会行为;能源生产和使用;通信技术与网络;政府运作和政府内部各级协调和治理,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许多其它问题。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包括时间和专业能力的限制),联邦、州和地方等各级法院绝对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做到合理有效地立法。
不论国家的立法机关如何构成,针对特定问题进行标准细化这一工作,都必须由行政机构和相关专家承担起来。立法机关可以以行政机构、利益集团和利益相关者提供的材料为基础,决定有毒物质在周边空气和地下水的含量低于多少才是安全的,然后据此制定相关法律。除了空气和水之外,其它领域也是如此。然而,立法机构还会采取另一种方式,即对那些具有特定公共政策目标的法案,将其立法权授予行政机构,让行政机构决定是否通过。最后一种方式是直接授权行政机构,即通过国会授权法和(或)宪法条款授权的方式,让行政机构自己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制度。
不论行政机构如何获得制定政策和监督管理的授权,都需要建立正式的机制对其进行权力监督,防止它们以牺牲公民的个人权利、公平和公共福利为代价去追求各自的部门利益。如果缺乏权力监督,行政机构可能会走向自我扩张、扩大预算、增加自主权和机构懈怠的道路上去,可能会使追求行政便利成其为主导价值。功利计算往往忽视了产出更大规模公共物品所付出的代价。过去,政府机构曾未及时阻止儿童在放射性尘埃中玩耍,还以科学实验为目的,导致被分在控制组的“病人”不必要地痛苦死去,甚至虐待关押在公共精神卫生机构中的犯人和精神病人,并对犯罪嫌疑人使用过度的非法暴力。[7]井蛙之见、资源的不足、错误的组织文化则是导致上述问题和类似错误决策和行为的基本原因。
立法监督、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就是抑制上述错误行政行为的基本方式。然而,这些监督是回溯性的,即危害发生之后,监督管理用随其后。与此不同,行政法要求行政机构在规章制定,行政执法、行政裁定和透明度等问题上严格遵循相关程序,同时还要求行政机构关切各种公共价值,只有这样,行政法才能对无视规则、滥用职权和低效无效的行政行为起到互补的和更为积极的监督作用。
行政法的一个缺点是它的一刀切倾向,即将所有行政机构纳入统一的程序性和实质性约束之中。当然,可以通过微调行政法要求的方式降低这种倾向。行政法面临的重要挑战,就是如何有效平衡监督行政行为与扼杀行政行为间的关系。为了在规章制定、行政裁定、行政执法、透明度和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建立这种有效平衡,美国政府于1946年开始实施了《行政程序法》。本文的重点工作就是对这部法律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进行深入分析。
二、规章制定
规章的定义是:“行政机构发布的具有普遍适用性或特殊适用性,并对将来生效的文件的全部或一部分,其目的在于实施、解释、规定法律或政策,或规定机关的组织、程序和活动规则。”[8]在美国,行政机构制定三类规章,即程序性规章、解释性规章(也称“说明性规章”)和立法性规章(也称“实体性规章”)。程序性规章面向行政机构的内部组织及运作。比如,如何申请福利和驾照,如何对由行政机构造成的损害提出赔偿要求,如何对不当行政决定提起上诉。解释性规章则具体说明了行政机构如何理解自身的法定权力、使命、政策和规章。举例而言,如果法规中某个术语意义模糊,行政机构就会出台相应的解释性规定。有些影响很大的案件就涉及到对某些术语的解释,比如空气污染和水运航道的“固定污染源”以及“专业开发”的人力资源测验。[9]根据当前的判例法,如果国会并未就某些条款做出明确说明,行政机构便有权采取任何合理的解释,并有权依据经验自行对原先的解释做出修正。[10]立法性规章基本等同于成文法,并具有法律效力。透明性要求所有规章都应在《联邦公报》上公布,但行政法只要求上述三类规章中的立法性规章执行这一规定。
(一)立法性规章的价值取向与关注点
立法性规章充斥着多种价值标准,某些价值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这些价值包括:
1. 灵活性:让行政机构凭借其专业知识和判断力寻求更先进的规章,从而更好地满足公共利益。
2. 政策标准:能确保行政机构充分考虑特定的公共价值,比如环境保护。
3. 忠于立法:,本意防止行政机构误解法规原意,或以自身的偏好替代立法机构的偏好。
4. 正当性:要求规章本身及其创设过程的合理性。相关成文法可能要求行政机构制定规章时使用最优质的信息。2000年《数据质量法》支持将同行评审、可重复性研究作为制定立法性规章的基本条件。
5. 参与:利益相关者与包括公众个人在内的其它利益团体的参与。
6. 效率:通常也包含时效性在内,是公共行政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诉求。效率可能也涉及行政机构的解释能力、执行能力以及减少诉讼案件量。如果花费九年时间为花生酱设立标准,或者花费两年时间决定薄土豆是否可以以炸薯片的名义进行销售,这样的行政机构的效率就是值得怀疑的。[11]
7. 解释能力、整合能力和执行能力是确保规章有效实施的重要条件。如果规章实施对象不能正确理解或遵守相关要求,规章落实效率就会被打折扣。类似地,如果检查人员或其它执法机构对规章的理解出现偏差,执法就会不协调、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
除了这些价值标准,比尔·克林顿总统第12866号行政命令还提出了指导行政机构制定立法性规章的12项原则,它们是:1)识别所要解决的问题;2)评价现有法规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作用;3)确定对现存法规的替代性法规;4)考虑风险问题;5)成本效益评估;6)权衡成本与收益;7)以最优质信息为基础进行决策;8)识别与评估可供选择的其它法规;9)征求州政府、地方政府和印第安部落政府的意见;10)确保法规间的协调性和一致性;11)尽量降低对社会的负担;12)使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在这张清单的基础上,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第13563号行政命令又增加了对“经济增长、创新、竞争……创造就业”以及“平等、人格尊严、公平和分配效应”等公共价值的关切。
除了平衡过多的价值标准和规范指南,行政机构的内部协作与府际协作也是一个挑战。奥巴马总统的命令号召相关机构“协调”跨政府的规章制度。依据1980年《文书削减法》规定设立的美国预算管理局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其主要工作就是协调。从根本上讲,依赖于联邦政府行政机构的政策标准,协调这些标准并取得标准的一致性,就是该办公室的主要使命。然而,该办公室对独立监管委员会的规章制定不具备约束力,这些监管委员会包括联邦通信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与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等。进一步地,行政命令还可能包含免责说明,这就使得这些行政命令在司法上不具可执行性。比如,第13514号行政命令(2009,第20部分第d条)指出,本命令不“创造任何权利或利益”,“不创设任何实质性、程序性或强制性的普通法或衡平法,不会使用这些法律反对国家、政府部门、行政机构以及政府组织的官员、员工、政府代理人和其它任何人”。
(二)立法性规章制定的类型
在《行政程序法》及其派生性法规授权或允许的规章制定程序中,类型不同,其所反映的价值取向也就不同。
1. 可免于行政法规范性要求的规章。豁免的范围包括涉及军事和外交事务、机构和人事管理、公共财产、贷款、津贴、福利与合同等内容的规章。不仅如此,只要有“正当理由”,比如程序标准不切实际、没有必要或不符合公共利益,行政机构都可免于行政法的程序性要求。
2. 非正式规章制定,也叫做“公告—评论”。这类规章制定是联邦监管性规章制定的主体。在非正式规章制定中,程序性规定要求:首先,行政机构应在《联邦公报》上发布规章建议稿;然后,吸收并考虑公众意见,当然也包括利益集团和其它实体组织的意见;最后,在《联邦公报》上公布最终制定的规章,并应给予相关方至少30天的缓冲适应期,当然,紧急情况除外。同时,《行政程序法》也授权相关利益群体,使其有权在最终的规章发布后仍提出诉讼,要求改变或废除该规章。
3.正式规章制定,也叫有案可查的规章制定。和司法审判类似,该类型规章制定过程十分复杂。它要求召开由陪审团、行政法官和其它官员主持的正式听证会。参与听证会的相关方提交证词和证据,并有可能受到盘问。听证会的全部文字记录将会被保存。主持会议的陪审团或官员先做出初步裁决。一般而言,这些初步裁决都会成为最终裁决,如当事人提出异议,初步裁决就成为建议性裁决,并接受行政机构负责人、管理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的审查。在个别情况下,依据审查结果,行政机构可能会发布针对当事人意见的试探性裁定和可能的修改方案。虽然正式规章制定的过程不需要严格遵循《联邦证据规则》,但任何最终规章都必须有实质性证据的支持,且必须完整地记录在案。《行政程序法》给行政机构提供了非正式规章制定和正式规章制定的选择。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不必要且是费时与低效的,除非存在针对行政机构的单行法,或者与规章相关的主题还存在争议,正式规章制定的基本过程通常都会被回避。通过正式规章制定的最终规章在《联邦公报》上发布后,至少再过30天才会正式生效。
4.混合型规章制定。为了形成某一令人满意的规章,行政机构觉得采取非正式规章制定方式不够充分,而正式规章制定又过于繁琐或没必要时,混合型规章制定就会被采用。较之于非正式规章制定,该类规章制定增加了行政机构举办的具有公告和评论形式的公众听证会。这些听证会会在全国各地举办。在听证会上,代表们讨论并对建议稿提出修改意见,或者建议撤销意见稿。听证会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平台,这种方式可能比仅仅分析书面意见更加有效,但同时会提高时间和经济成本。
5.协商型规章制定。作为另一种提高规章制定过程效果和效率的方式,协商型规章制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起来。1990年的《协商行政立法法》授权行政机构成立规章制定委员会,该委员会通常由来自行政机构、利益集团、利益相关者和公民社会组织的25名成员组织。“协商行政立法”被认为是一种比非正式的、正式的,或混合型规章制定更能解决问题的规章制定方式。在实施协商型规章制定过程中,一致同意是达成规章草案的必要条件。即便如此,行政机构也还是要提交规章草案,对其进行公告和征集意见,在此过程中,如有反对意见,规章草案也有可能得到修改。至于协商型规章制定是否履行了促进时效性和减少诉讼量的承诺,这还将是一个持续争议的问题。[12]
除了正式规章制定,其它四种方式都不算过于繁琐。然而,司法裁决要求详细说明规章草案的范围和目标,行政机构对相关评论的回应,并对规章基本原理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就迫使行政机构进行规章制定时提供更为详实的材料。很多成文法和行政命令要求关注环境可持续性、环境正义等特定价值与小企业、家庭等群体利益,要求信息与法律事务办公室的审查,要求采取同行评审、可重复性研究、成本收益分析和其它考量,很显然,这就延缓了规章制定的进程。1996年的《国会审核法》要求进行立法审查,还要求提供最终规章的否决可能性,这就使规章制定进一步复杂化。虽然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项规章在此过程中被否决,但《国会审核法》规定的立法行为还是起到了较大作用,同时,被否决的潜在可能性可能促使行政机构在制定规章草案和最终规章之前与相关国会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进行商议。为应对《行政程序法》实施后规章制定中出现的新特点,部分学界和实务界人士认为,当前的规章制定已很“僵化”,现在是时候对指导规章制定的各种价值标准进行优先排序和简化了。[13]
三、行政裁定
行政裁定也是行政机构常用的决策方式。在某些方面,规章制定和行政裁定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两种替代性方式。行政裁定应用于以下领域:决定个人是否具有享受福利的资格;解决不公正或非法的经济、人事和劳动关系方面的指控;授予许可证或拒绝授予许可证;强制实施相关法律或规章制度以保护公众、环境、企业以及与威胁、有害行为、疾病、危险作斗争的组织。在美国,行政裁定的结果被称之为“制定秩序”。
行政裁定和规则制定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二者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相互替换的。行政裁定是回溯性的,它适用于特定的个人或公司等实体,且关注于“裁定事实”而非“法律事实”。裁定事实涉及个人动机、目的和行为,而法律事实通常与公共政策制定相关,并可能以现代公共政策研究普遍采用的政策分析为基础。不过,行政机构的一个裁定,可能就建立了一个公共政策,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该裁定中的当事人。比如,针对某一特定情形,如果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做出特定的行政裁定认为,某个特定雇主一直从事不公平的劳资关系实践,那么,在该委员会管辖范围内,该裁定就会成为一个先例,并将广泛应用于未来的雇佣关系实践,所起的作用就像通过规章制定形成的一个法规。在多数情况下,行政裁定并不需要考虑诸如环境正义等公共价值。因此,较之于规章制定,行政裁定所关注的价值集合通常较为狭小。
(一)行政裁定的价值诉求
引导行政裁定的价值观包括:1)公平;2)胜任力;3)效率;4)对行政绩效良性或积极的影响。
行政裁定是否公平,可由行政裁定的当事人对自己是否受到了公平的对待以及对裁定结果本质上是否公平的感知两个角度加以测量。行政裁定是否具有胜任力,可由行政机构是否维持初步裁定和法院是否维持行政机构的最终裁定加以评价。如果行政机构的初步裁定和最终裁定在上诉中经常被法院推翻,那么行政裁定的胜任力就值得怀疑了。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联邦劳资关系局所做出的行政裁定,往往出于一些非实质性问题的原因而被联邦法院否决。[14]一些法院判决直接指出(某些案件中)行政裁定缺乏胜任力。在一个案例中,法院呼吁联邦劳资关系局,希望该局提供“一种能让当事人理解的方式”解决冲突。[15]在另一个案件中,法院认为,不论行政机构(的裁定)是对是错,“联邦劳资关系局陈述的裁定理由肯定是错误的”。[16]需指出的是,这里被感知的无能并非出于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对工会或管理的喜好这样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效率涉及时效性问题。行政裁定对行政机构的运行会造成冲击,且这样的冲击会对行政机构的绩效产生一定压力。因此,如果行政裁定过程缓慢、昂贵、复杂,其结果某种程度上就会非常繁琐或麻烦,公共管理者和其它人员就不愿采取它。美国联邦政府中所谓的“庸人”问题,也许就是最好的例子。约三分之一的联邦工作人员认为他(她)们的机构并未采取可能包含行政裁定等相关措施解决庸人问题。同样,自认为遭受非法歧视或性骚扰的个别工作人员不愿提请行政裁定,也正是因为此程序极其繁琐和漫长。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百分之六的联邦工作人员声称遭受性骚扰并采取了正式行动,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她)们认为采取正式行动在短期内非但不会有效的帮助他们改变他(她)们的现状,反而还会影响他(她)们的职业发展。但如果大部分受迫害的人都认为行政裁定制度不起作用,他(她)们的个人遭遇就会直接影响组织绩效,而且难以得到纠正。[17]
同时体现公平、胜任力、效率等价值观并取得良性或有利的影响,可能是很困难的。在联邦政府,国家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所做的行政裁定总会遭到严厉批评,因为这些裁定既不公平,也没效率。如上所述,联邦劳资关系局所做的行政裁定的胜任力也曾出现严重问题。考绩制度保护委员会被认为是联邦政府中最具行政裁定能力的机构,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基本没有驳回该委员会所做的行政裁定。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该委员会就无可挑剔,其主持的关于不良人事行为的行政裁定制度,也被公认为是造成“庸人”问题的主要原因。
(二)行政裁定的制定
作为一种决策制定形式,行政裁定一直遭受批评。除了法官和法学研究者外,其它人很少会接触到通过行政裁定建立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可能埋没于大量复杂的判例法之中,而这些判例法需要很强的技能才能使用它,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才能理解它。因为是通过回溯过往行为的方式进行,所以行政裁定经常被称为“狗法”。就像训练一只狗,只有涉入行政裁定的当事人已经触犯法规之后,才会被认定为做出违法之事了,而这些法规或是以前从未被明确的,或是需要认识掌握大量判例法才可避免的。在解决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时,行政裁定既不采取集体的形式,也不采取参与的形式。它往往是一个对抗式的过程,即有赢的一方,也有输的一方。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不是此类事业的显著特点。因此,行政裁定的当事人不会自动展现那些可能对自身有害的信息。而且,在裁定过程中,各方可能会相互攻击对方提供的信息乃至对方的品德。
最后,行政法官、政府特派调查员和陪审团做出的各个行政裁定,其结果可能并不一致。当这类裁定发生于相关法理本身就不清晰的情况时,至少有一方将遭受不公正对待。比如,在1987年的专业航空专家协会、航洋工程师福利协会、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诉联邦劳资关系局的案件中,某联邦上诉法院认为“在当前两种情况中,联邦劳资关系局由于不能恰当阐明其监管规则,其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的违规行为,一个行政法官判定要支付欠薪,另一个的判定却不同。......联邦劳资关系局中的混乱和前后矛盾现象十分明显。因此,该局有义务对其选择制定的任何规章做出合理解释,包括对偏离其自身法律主体的规章做出解释。”[18]
虽然行政裁定存在上述问题,但从行政角度说,它依然有很多可取之处。第一,它通常给行政机构提供了相当大的自由度,让行政机构自由决定使用执法资源的时间和地点。为了更快地解决案件并获得大量成功执法记录,行政机构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对那些较弱的违法者,假定他(她)们违反了相关规章制度,并以此进行行政裁定。这种方式可能会让行政机构招到更多的法学院毕业生,这些毕业生需要的就是进入私人法律事务所之前获得更多的诉讼经验和胜诉记录。或者,行政机构可以选择追捕大号主犯,以便在实现机构使命中做出更为清晰和更有影响力的政策声明。
第二,有些新技术、新程序和新活动需得到不断发展,但在监管上却没有明确适用的法律和法规,这种情况下,行政裁定比规章制定更加可取。成文法和其它法规之所以使用“公共利益”、“公平”、“不公平”、“正义事业”、“合理”、“不合理”、“适当”等词汇,正是因为我们很难也不可能把所有符合条件的情况(或情形)一次性描述齐全。它们的含义必须在可观察的经验中被定义。比如,在2010年加利福尼亚安大略市诉讼案中,最高法院指出,“在使用政府雇主提供的电子设备进行通讯的情况下,应当十分审慎地应用隐私期望的整体概念。在其社会作用并不清晰的新兴技术问题[19]上,法官如果过于应用第四修正案,则可能会出现错误”。通过判例法的逐步发展,行政机构不需要致力于规章制定就能不断调整完善它们的政策。
(三)裁决形式
在美国,《行政程序法》或多或少为行政裁定的形式提供了准则。当发起一场行政裁定时,行政机构必须告知相关方听证的时间、地点、性质、行政机构依赖的法律根据和管辖权限、裁定需要考虑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听证会的安排一定要考虑利益相关方或其代表的便利性。这些相关方有权展示事实、论据、解决办法,并要求改变裁定的时间和性质。听证的利益相关方拥有以下权利:
1.由自己聘用(而非行政机构提供)的律师代表自己权利;
2.在“合理的时间”内做出听证结论;
3.及时通知听证结果。否决相关申请或其它要求时,应提供一份简要的解释性说明;
4.裁定必须建立在实质性证据的基础上,并完整记录在册;
5.当行政机构自己不主持听证会时,要任命中立的行政法官(源于“政府特派调查员”)或其它人员主持听证会;
6.确认事实时,利益相关方有机会口头或书面地展示相关情况,并有必要在反驳和质证环节中提交相关证据;
7.保存好一份完整和唯一的记录,包括证词的记录;
8. 关于行政法官的发现、结论以及对相关事实、法律和自由裁量权的推论的声明;
9. 对行政机构最终行为的司法审查。
(四)非诉讼争议解决机制
和采用规章制定一样,行政裁定已变得更加正式、耗时,且逐步变得复杂起来。这就提供了寻求非诉讼争议解决机制的动力。1990年的《行政争议解决法》中增加了联邦行政法规允许和管理的所有解决争议的过程方法。修订后的《行政争议解决法》还允许行政机构采取包括仲裁在内的多种非诉讼争议解决技术。然而,该法也提醒以下情形不适应采取非诉讼解决机制:涉及公共政策的问题、一致性很重要的问题、可能强烈影响第三方的问题,或者行政机构需要保持开设先例权的问题、行政机构需要保留对相关政策具有管辖权的问题。仲裁既可以具有约束力,也可以仅具有咨询性质;可以自觉受到《行政争议解决法》的约束,也可以不受其约束。除了仲裁,在公共行政领域,标准的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还包括各行政机构的申诉专员。因错误管理或低效无效管理产生的受害方或其代表向申诉专员提起上诉,申诉专员就会试图解决这些行政错误。在第三方调解中,各方相互谈判,并努力找到一种共赢或至少是各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第三方调解与仲裁(调解-仲裁)相结合,可以尽可能多地解决问题,而不用将这些问题都提交仲裁者或陪审团解决。引导比调解干预的更少,但达到的目的却差不多。如果核心问题是经验性的,比如公司广告是否是虚假骗人的或者某公司行为是否对另一公司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那么,实情调查就派上用场了。当然,小型审理和模拟审理有时也会被采用。
较之于行政裁定,除了低成本和高灵活性的优点外,调解和引导的方式可在行政法官或仲裁人等第三方较少涉入的前提下就处理好各方的分歧。这种方式可能开创这样的局面,即双方都将参与处理问题的过程之中,并觉得自己对问题的处理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同时,这种方式虽有时被视为非强势性的处理方式,但它确实对非诉讼争议解决机制提供了持续性的管理支持。
四、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在现代政府普遍存在,因此我们很难对其进行概括。首先,它涉及类型各异的活动。比如,环境问题、产品安全问题、人力资源监管问题,这些问题差异很大;第二,太多的执法依赖于基层检察员和调研员,在同一监管领域,差异也非常大;第三,行政执法类型从消极到积极,并且包括“回避主义”、“调和/宽松”、“灵活”与“墨守成规”等类型[20];第四,这些执法类型可能导致实际行政执法过程中,或者过于宽松,或者过于严苛,或在综合考量资源有限性和结果有效性这一矛盾体的基础上,在宽松执法与严苛执法中采取折中主义;第五,监管既可能是事后的,也可能是事前的,还可能是全过程的;第六,行政执法既可以基于威慑,也可以基于教育、说服;第七,与监管对象的合作、中立或者对立关系是划定和分析行政执法类型、内涵的重要基础。最后,处罚既可以是刑事性质的,也可以是民事性质的,具体方式包括罚款、查封产品、召回产品、撤销或暂时吊销许可证、暂停或终止销售许可等。
在美国,行政法很大程度依赖于对监管对象的强制性信息要求,这些要求包括认证、检查、检测。检测既可能在产品上市前,也可能在产品上市后。经过检测,产品可能被召回,也可能被查封。任何执法方式都会受到包括行政法在内的各种法律限制。《行政程序法》并没有授权行政机构调阅案卷和传唤当事人,也没有一定要将各成文法授予《行政程序法》的权力(如果有的话)转授给行政机构。检查、查封和检测都受到宪法关于禁止不合理搜查与抓捕的限制,即要求行政机构进入或以其它方式搜查工厂之前,必须获得搜查令。
现代行政学理论和行政实践经常偏好与监管对象的合作关系,也希望监管对象能自觉遵守相关规章制度。不讲人情的严格执法通常不受欢迎,而与监管对象的伙伴关系则更受青睐。这就意味着在实践中,大量行政执法会通过“监管对象自我检测和自我报告,监管机构再行检查”的方式进行。即便如此,这些行政机构仍经常保持对违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可能性
五、透明性
行政法也要求政府具有透明性。透明性通常体现于有关自由信息和公开会议的相关法律之中,且被认为有助于实现官员问责和公民的知情权。在1946年,联合国决议指出“信息自由是基本人权,是联合国奉为所有神圣自由的试金石”。[21]然而,出于国家安全、执法、其它政策的考虑,也为了更好地从个人和私人机构获取信息,政府必须对某些信息进行保密。行政法的任务就是做好公开与保密的平衡关系。
1966年通过并经过不断修正的联邦《信息自由法》,原则上要求所有信息公开,同时允许某些信息免于强制披露,该法力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公开与保密的适当平衡。得到豁免的信息不认同诸如公开这样的价值。得以豁免的信息包括:
1. 被划定为机密的有关国防或外交政策的信息。
2. 纯属行政机构内部的人事规章和工作制度。
3. 其它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公开的信息。
4. 第三方的商业秘密以及第三方向政府提供的含有特惠或机密情况的商业、金融信息。
5. 政府机构以外的当事人同政府机构进行诉讼时, 在法律上不能利用的机关内部或机关之间的备忘录或函件。
6.公开后会明显侵害个人隐私的人事、医疗档案以及其它类似的档案。
7.“为执法目的而搜集的调查记录或相关信息,但仅限于如果豁免前述‘调查记录或相关信息’就会发生以下情况:(A)很可能会干涉执法过程,(B)剥夺个人接受公平审判或公正裁定的权利,(C)可能会对个人私生活造成不当侵犯,(D)可能会暴露秘密消息来源的身份,包括以秘密方式获取信息的州政府、地方政府、外国机构或任何私人机构,或者,刑事执法机关在刑事调查过程中搜集的记录,或者行政机构进行合法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情报调查,或透露纯属秘密来源提供的机密情报,(E)如果透露就可能产生规避法律的风险的情况下,透露执法调查或检举起诉的技术、程序或指导准则,(F)可能对任何人的生命或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8.金融监管部门为监管金融机构而使用的信息。
9.包括地图、矿井在内的地质和地球物理的信息。[22]
信息自由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诉讼。除了上述第7条C款之外,请求人无须接受身份要求。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任何人可以要求任何信息,即便没有他/她不具备美国公民或居民身份。一个联邦行政机构不能通过《信息自由法》直接从另一联邦行政机构获取信息和情报。该法的运行形式是通过查询者要求信息而不是媒体传播信息给公众的方式而运行。提请信息要求就会引发相关活动、行为。虽然没有固定格式,美国司法部印发了《<信息自由法>参考指南》,为每种信息要求都提供了模板,其它机构也在网上提供了在线申请表。查询人有义务详细描述其所需信息的特征,以便于负责实施该法的机构工作人员查找。查询人可能需要支付查询和复印费用。费用多少取决于被查询信息的目的。《信息自由法》的使用范围仅包括存在于行政机构电子报告中的现有记录和原始统计数据。查询人可以要求一个行政机构提供关于某个名人的相关记录,但不能要求行政机构提供分散于该名人身上的所有信息。行政机构可在20天内告知查询者所要的信息是否会公开,如行政机构拒绝查询者的要求且查询者对此提出复议,则行政机构须在20天内做出回复。如果政府需进一步澄清什么信息是查询人的真正所需,则该期限可以延长10天。当行政机构同意查询人的请求,则公开该信息没有时间限制,可以是一年,也可能更久。如果拒绝查询人的申请,行政机构可能被上诉到联邦地方法院。此时,行政机构就要承担一定的压力,即要证明被拒绝的信息申请在上述九个豁免对象之内。
第4、5项豁免条款和第7项C款豁免需要简要的说明。在第4项豁免条款中,出于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该项豁免条款已引发了“反信息自由诉讼”。商业机构可以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防止它们的商业信息和商业秘密被公开出来。1987年的第12600号行政命令要求,行政机构必须告知商业组织它们的商业信息已被“信息自由”了。如果行政机构披露信息是武断任意的,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或是没有遵循法律的话,则该披露就违反了《行政程序法》的第706部分,因而该信息就不应该被公布出来。包括1948年《商业秘密法》在内的相关成文法,就特别规定了禁止公布某些商业信息。
第5项豁免条款针对的是未纳入行政机构决策的预决策信息。其目的是为了允许行政机构的决策者在制定草案(或草稿)过程中,可能提供一些非常规的、“不成熟的”,甚至是看似不现实或漫无边际的想法时,不会因为其意见、评论可能被公开而患得患失。
第7项C款豁免条款,即保护个人隐私的条款要求查询者说明使用该信息的公共利益诉求。如果该信息不能增进公共利益,则对该个人隐私的侵犯就是“没有根据的”,该信息的公开也就自然得以豁免。第7项C款豁免条款也允许该个人的其它家庭成员试图维护他(她)们的隐私利益。该豁免条款还允许一个人的其它家庭成员试图维护当事人自身的隐私利益。
1978年的《总统记录法》确立了总统文档中的透明性原则,并明确规定总统文档属于政府而非总统个人所有。该法授权美国国家档案馆馆长于总统任期结束12年后发布该总统的相关书面文档、录用文档以及其它形式的文档。一般来说,国家图书馆馆长会依据《信息自由法》原则扣留相关材料。然而,不像《信息自由法》第5项豁免条款所覆盖的,不能只是因为其所披露的是白宫内部的讨论或参谋意见,馆长就扣留相关信息。前总统或前副总统可以要求禁止馆长拥有对相关文档的发布权限,这里的相关文档指的是他(她)们所认为的受成文法或宪法授予的行政特权所保护的文档。基于三权分立原则,依据宪法,行政特权允许总统对国会和最高法院保留相关机密信息。
(一)隐私
政府掌握如此之多的公民个人信息,因而,透明性原则不可避免地会与隐私存在竞争,这在第7项豁免条款中有明显地陈述。1974年的《联邦隐私权法》监管着对公民和永久居民信息的搜集、管理和发布等相关工作。主要地说,该法案提供了:
1. 使个人有权查阅档案并确保记录的准确性,这主要通过为个人创设权利得以实现。这些权利包括:检查行政机构对其所做的相关档案,要求政府改正错误档案,如行政机构拒绝改正,则个人可在该份档案上做出异议说明。中央情报局和执法记录不受此款法规限制。
2. 档案管理要求行政机构就档案系统如何进行访问、存储、处理及其它相关事宜在《联邦公报》上做出具体说明。该法案也规定,使用有关个人材料的档案的目的必须与行政机构的使命相关,行政机构也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出现信息错误。
3.要求获得当事人同意的规定限制了对个人信息的披露。然而,也存在十二种特例,其中包括面向国会、各级政府的执法机构以及遵照《信息自由法》相关要求的查询。更为经常的是,发布有关个人的档案可能仅仅是因为“日常使用”,“日常使用”被循环定义为“为了与其搜集目的相协调的目的”。[23]如存在卫生或安全等令人信服的原因,则披露个人信息也是被允许的。[24]当为了满足《信息自由法》要求而发布个人档案信息时,在信息贡献问题上,增进理解政府运作的公共利益必须与对应的受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利益相平衡。[25]
(二)公开会议
1972年的《阳光法案》和1976年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都包含了公开会议的相关行政法条款。这些成文法通过正式会议上的口头讨论并对公众公开,对《信息自由法》做了有效补充。通常,这些讨论也产生若干有限的书面记录。《阳光法案》适用于各种联邦管理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批准。这样的委员会在联邦政府中大概有50个。这些行政机构被要求会议一周前就发布会议通知。该要求原则上适用于任何参会人数达到法定标准的各种委员会。有些会议同时适用于《信息自由法》的豁免条款,这样的会议可能就不会被公开。然而,《信息自由法》第五项豁免条款保留决策前讨论信息记录的授权不适用于此。在非公开会议中,行政机构必须保存相关文字记录、录音记录和相关备忘录,如会议非公开的理由不适当,则这些记录将随即被公开。
《联邦咨询委员会法》要求召开咨询委员会会议须在《联邦公报》上发布通告。利益团体可以参会,可与委员会面对面,也可提交申明报告。该法还要求,委员会会议的详细会议记录须和诸如报告、研究报告和工作底稿等材料同时保存好。如存在类似《阳光法案》下被允许非公开会议的理由,则咨询委员会会议也可以关门举行。
(三)举报
行政法也通过保护举报人提高透明性。举报指的是揭露违反法律、规章制度,管理不善,滥用职权,对公共安全和健康具有实质性的、特定的威胁,以及“巨大浪费”等问题。[26]举报者的权利与政府运作的需要相平衡。自2006年最高法院对加西堤诉塞巴洛斯案的判决后,作为工作任务产出的录音和书面材料不再受到保护。任何受《信息自由法》豁免条款保护的信息也可能不再受保护。针对联邦巡回法院和考绩制度保护委员会,美国上诉法院对联邦泄密者保护的相关法律作了十分详细的解释,甚至经常到了咬文嚼字的地步。[27] 2012年的《泄密者促进法》又将保护范围扩大到举报上级主管和违法乱纪者。
虽然1978年联邦《文官改革法》和1989年的《泄密者保护法》都力图保护泄密者不受报复,但有些管理者还是将泄密视为“背叛”、“打小报告”或“告发”,因而泄密者在工作上经常会受到严重反响。因此,1989年的《泄密者保护法》中就包含了若干旨在保护泄密者不受报复的条款。
(四)告发人诉讼
告发人诉讼的法规会对报告政府合同方不良行为的泄密者进行奖励和保护。1863年通过并于1986年修订的《联邦虚假申报法案》授权泄密者可以代表政府起诉私人组织,以便获得欺诈赔偿。美国司法部也可能参与这些起诉。依据情况的不同,告发人诉讼的原告可获得赔偿总额的15%到30%,这可能是数百万美元的金额。从1986年到2006年,告发人诉讼案件共为联邦政府赢取18亿美元的赔偿。[28]
六、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在美国,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产生了高度详细、复杂的判例法,它们构成了联邦政府行政法体制的重要特征。长期以来,各联邦法院共同追求对法治和行政裁量权这两种竞争性价值的平衡。尽管在公共行政领域,自由裁量权被认为是必要的,相关方面也做了相当的努力确保自由裁量权以一种明智、专业与合法的方式运行。然而,在法律界,自由裁量权常被视为对法治的威胁。“法治的终点便是暴政的起点”这一著名警句,就展示在美国司法部总部大楼的显著位置。在美国法律眼中,自由裁量权与法治的关系,即使不是水火不容,至少也是存在争执的。在宪法判例中,最高法院法官称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为“邪恶的力量”。[29]
在平衡法治与行政裁量权的过程中,美国联邦法院将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严格程度视为一种变量,该变量可分为“严格型审查”到“宽松型审查”再到实际上的“不审查”等三种类型。严格型审查意味着深入的调查,它将给行政机构带去巨大的说服责任,其适用对象为行政机构规章制度的内容、修正和废止。在实践中,撤销一项从未颁布的规章,严格型审查可能就会要求行政机构执行另一规章制定的程序。[30]如某行政机构拒绝《信息自由法》的要求,就像纯粹的自由裁量行为一样,该机构也会受到严格型审查,但相对会比完全严格型审查稍微宽松些。[31]
当符合《行政程序法》或其它成文法的最低要求时,该行政机构规章制定的程序就应接受宽松型审查。行政机构对成文法授权的那些未加定义或定义不够具体的条款所做的解释,也需要接受宽松型审查。这种宽松型审查包括行政机构对其管理权限的法律解释。[32]
在特定的案件中,实际上的“不审查”,或者至少强烈反对司法审查的推定适用于行政机构不予实施的法律规章。在1985年赫克勒诉查内案[33]中,最高法院推定,因为对所有对象进行执法并不总是可行的,一个行政机构应该有决定往哪投入执法资源的自由裁量权。理论上讲,当无法可依时,《行政程序法》授权的“不审查”就起作用,如即使对禁止翻供进行审查,其力度也是十分轻微的。[34]然而,和很多其它行政法一样,特例总是存在的,在某些情况下,法院可以强制行政机构采取相关行动。[35]
七、结论
正如本文对联邦行政法的述评所阐明的,不认真对待行政法就等同于不认真对待公共行政。联邦政府的事务官和政务官既从行政法那里得到授权,也受到行政法的约束。如认为规章制定是联邦行政机构最为重要的业务,正像科尼利厄斯·科尔文振振有词般的主张,那么一个简单的证明完毕就足够了。[36]如科尔文的看法过于夸张,行政法也还是为公共行政的职能设置提供了核心框架。很显然,事务官和政务官既不是公共行政的一切,也不是公共行政的唯一,行政法才是中心。
这就提出了若干研究问题。第一,“公共管理者实际是如何进行管理的?”[37]这与公共管理文献提出的公共管理者应该怎样进行管理这一问题具有根本性的差别。[38]想要正确理解行政法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就应做到:首先,公共行政学界应当给予行政法更好的认识;第二,应该认真观察行政法如何影响行政决策的制定和其它行政活动。考虑到公共行政中各种复杂事物间的多重因果关系,除了数据分析、因果关系模型和其它不以直接观察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之外,还可能需要进行定性研究,或至少大量的调查研究。虽然案例研究在公共行政学界并不受欢迎,但在上述问题上,它可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构建价值。
第二个研究问题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即行政法如何影响对公共机构使命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立法性决策。比如,在2013年的德州阿林顿市诉联邦通信委员会案中,最高法院认为,有关行政机构法律解释的雪佛龙法则 (Chevron Rule)让国会认识到,立法中的模糊性将首先被行政机构解决,这种模糊性让行政机构(而不是法院)具备模糊性所允许的最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针对国会可能的立法,雪佛龙法制提供了一个某行政机构的现存定义:只要在合理的解释范围内,由行政机构而非法院对成文法的模糊性做出解释......国会知道,想要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就使用简单的语句,而欲扩大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权,那就使用复杂的语句。[39]
雪佛龙法则会否因此助长了违背道德的风险,即国会议员将不通过立法程序进行复杂的政策选择而是把权力委托给行政机构,这可能会成为行政法驱动的重要研究问题。在构建行政法过程中,通过授权,有些国会议员就逃避了他(她)们的立法责任。[40]1980年的最高法院关于产业联合部、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诉美国石油协会案[41]就印证了上述说法。
最后,还有很多关于司法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的学术问题,该类问题涉及宪法契约、法治问题与行政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冲突,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决策形式、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透明度等问题。美国的法院有时被视为公共行政“伙伴”。从某种程度上讲,情况就是这样:正如行政法一样,如果公共行政理论在公共行政实践中被充分践行,这样的“伙伴关系”就应该得到更好地研究。
毫无疑问,行政法体系中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正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行政法。
[参考文献]
[1] David H. Rosenbloom. Reflections on Public Administrative Theor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3,43(7).
[2]The Status of Law in Contemporary Public Administrative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Practice. in R. OLeary, D. Van Slyke, and S.H. Kim, eds. The Futur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round the World: The Minnowbrook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 USA: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0.pp211-220.
[3] Zeger van der Wal. Value Solid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Vrije University, Amsterdam, Netherlands, 2008.p56.
[4]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Task Force on Educating for Excellent in the MPA Degree. “Excellence in PA Report, Part 2”. PA Times ,2008,31(6).
[5]David H. Rosenbloom. Administrative Law for Public Managers(Second ed.). Boulder, Colorado, USA: Westview Press, 2015.
[6] http://www.eolss.net/sample-chapters/c14/e1-34-05-07.pdf.
[7] David H. Rosenbloom, Robert Kravchuk, and Richard Clerk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ing Management, Politics, and Law in the Public Sector, (eighth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2015, p368, 534.
[8] APA, 5 U.S. Code 551(3).
[9] Griggs v. Duke Power Co., 401 U.S. 424 (1971); Washington v. Davis, 426 U.S. 229 (1976), Chevron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467 U.S. 837 (1984).
[10] Chevron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11][17] Rosenbloom. Administrative Law for Public Managers, Boulder, Colorado, USA: Westview Press, 2015.p67,pp95-99.
[12]Cary Coglianese. Assessing Consensus: The Promise and Performance of Negotiated Rulemaking. Duke Law Journal ,1997,46 (6).
[13] Jason Webb Yackee and Susan Webb Yacke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Bureaucratic Performance: Is Federal Rule-Making ‘Ossified’?.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0,20(4).
[14] David H. Rosenbloom. The Federal Labor Relations Authority. in P. Ingraham and D. Rosenbloom eds.. The Promise and Paradox of Bureaucratic Refor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2.pp141-156.
[15] American Federation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Local 32 v. Federal Labor Relations Authority. 774 F2d 498, 506,1985.
[16]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v. Federal Labor Relations Authority. 770 F2d 1223, 1226-1227,1985.
[18] 809 F2d 855, 860,1987.
[19] 130 S.Ct. 2619, 2629,2010.
[20] Robert Kagan. Regulatory Enforcement. in David H. Rosenbloom and Richard Schwartz eds.. Handbook of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94, pp387-390.
[21] Spencer Zifcak. Freedom of Information. in Jay Shafritz,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Boulder, Colorado, USA: Westview Press, 1998, p942.
[22] APA, 5 U.S. Code, section 552[b][1–9].
[23][24] 5 U.S. Code, section 552a.
[2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v. Federal Labor Relations Authority. 510 U.S. 487,1994.
[26]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 of 1978, section 1206[b].
[27] See U.S. 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s for Federal Employees. 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 USA, U.S.
[28] For a discussion of qui tam see David H. Rosenbloom and Ting Gong. Coproducing ‘Clea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xamp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ublic 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Review, 2013,36 (6).
[29] Delaware v. Prouse, 440 U.S. 648,1979.
[30] Motor Vehic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v.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463 U.S. 29,1983.
[31] Citizens to Preserve Overton Park, Inc. v. Volpe, 401 U.S. 402,1971; Universal Camera Corp. v.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340 U.S. 474,1951.
[32] City of Arlington, Texas v.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133 S.Ct. 1863,2013.
[33] 470 U.S. 821,1985.
[34] Schweiker v. Hansen 450 U.S. 785,1981.
[35] Massachusetts v.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549 U.S. 497,2007; Kim Morris. Judicial Review of Non-reviewable Administrative Action.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9 (Winter): 65-86.
[36] Rulemaking(second edition). 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 USA: CQ Press, 1999. Q.E.D, quod erat demonstrandum.
[37] How do Public Managers Manag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Jossey-Bass, 1995.
[38] 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 USA: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1.
[39] 133 S.Ct. 1863, 1868,2013.
[40] David H. Rosenbloom. Building a Legislative-Centere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1946-1999. Tuscaloosa, Alabama, U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0.
[41] 448 U.S. 607.
Taking Administrative Law Seriously in Contempora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David H. Rosenbloom Helenak. Rene
[Abstract]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widely considered to incorporate perspectives based on management, politics/policy, and law. However, law is not prominent in contempora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literature and is also neglected in many accredited U.S.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ograms. Administrative law is the body of law that regulates public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making and action. It is where well-developed public managers must manage within its frameworks and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explains what administrative law is, why it is important, and, by way of illustration, the values that inform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devoted to rulemaking, adjudication, enforcement, transparency, and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Keywords]rulemaking, adjudication, transparency, judicial review
[Authors]David H. Rosenbloom i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American University,Washington, DC,USA; Helena K. Rene is Program Development Consultant,School of Professional and Extended Studies American University,Bethesda, Maryland,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