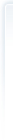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地区族群认同与社会治理研究》(批准号:08CZZ010)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国家的使命是协调冲突、创造秩序,其力量体现为公共权力及其运行。因此,人们通过建立使公共权力得以确立和运行的制度体系来建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扮演了重要的力量。现代国家的发展使提升和整合文化成为重要内容,将文化塑造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使国家治理融于文化塑造之中,必将成为民主时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软治理;文化;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09)03-0122-04
一、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国家
在现代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常态的内容,即拥有最高主权、明确的国土边界以及由明确国籍身份和国家认同的公民所构成的国家。对于这样的国家,著名人类学家安德森将其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种判断是基于他的认识:“事实上,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1]他认为,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现代国家的兴起主要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事实上,无论是古代国家还是现代国家,都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差别,是各自想象的方式不同。既然都是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方式再怎么不同,都离不开想象本身。想象是一种意识形态,涉及信仰、符号、观念、心理以及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工具——语言。这决定了这种共同体的维系和发展离不开文化这个要素。从一定意义而言,文化所起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这与共同的文化一旦被认同就往往深入人心,并与人的尊严、信仰和信念紧密相连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一个国家的建立、维系和发展必须以对共同体的想象作为基础。如果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有着各不相同的想象,其认同也就必然不同。认同的差异和冲突必然带来共同体的龟裂、冲突,甚至是解体。为此,任何国家的确立都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组织、制度、宗教、习俗、权威以及传统等资源——在整个共同体内创造出共同的想象和认同,并通过家庭、学校、宣传等机制进行政治社会化,将共同的想象和认同在代际之间传递和延续。前者形成了国家努力推进的一体化行动,后者则形成了国家持之以恒的公民教育。通过这些过程,作为社会共同体存在的国家便能够在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认同和共同的理想下聚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然而,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看来,国家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一个社会体。在他看来,“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才是共同体的生活,“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相反,“社会是公众性的,是世界”,“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所以,“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2]依据这种标准,国家无论怎么看都不属于“共同体”的范畴,而是“社会”的范畴。也许在古代社会,国家与共同体之间还具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如传统中国的国与家。国家建立在社会阶级与阶层之间的紧张基础上,现代国家以社会成员的独立存在作为基础。所以,国家完全不属于共同体,仅仅是一种政治社会。国家的这种形态属性,决定了国家不是通过亲情、习俗、宗教来维系,而是通过公共意志、公众舆论以及制度体系来维系,其使命是要将分散的个体和组织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看到,国家本质上虽然不是滕尼斯式的“共同体”存在,但其发展和建立却是努力将社会整合为一个“共同体”,即相互依存、相互帮助、和谐共处、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这种发展动机很容易在各个时代的国家身上找到。正是因为这种动机的存在,国家才会在权力、制度和组织的资源之外,努力开发文化资源来整合国家。这样,国家不仅能够与其既有的共同体(如家庭、村落、宗教团体)保持和谐共存,而且能够使国家在丰富的文化资源基础上将自身整合为高度有机结合的共同体。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国家看作是努力使自身有机化的共同体。
对于作为共同体的国家来说,治理的使命主要有四点:一是保证共同体统一与完整;二是保证国家制度有效运行;三是保证经济与社会有效发展;四是保证社会成员获得自由、平等与安全。前两者是基础,如果完不成这两个使命,整个国家治理也就无从谈起,但是,这些使命的实现又或多或少必须建立在民众对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因此,国家治理最终依赖于公民的文化认同,文化是国家最可依靠的力量和资源。
二、文化:国家软治理的基础
人是国家的核心,制度是国家的架构,文化是国家的精神。一个国家的成长既取决于人的成长,也取决于制度与文化的发展。人塑造了制度与文化,反过来,制度与文化也塑造着人。这就决定了人的成长与制度、文化的发展相辅相成。在这样的发展逻辑下,国家的治理,既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发育,也有赖于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此外,还有赖于文化的塑造。由于文化所形成的权力和权威在国家治理中往往不是直接发挥作用,人们就把国家治理完全寄托在权力和制度的有效性上,忽视了文化在其中的价值与作用。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二千多年前思考城邦治理的时候,就十分强调文化在城邦治理中的价值与作用。在他看来,城邦的幸福与人的幸福一样,有赖于三个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性灵)诸善。一个好的城邦,不仅需要好公民、好政体,而且需要好德性。“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必须是在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3]道德是文化精神的核心,文化是道德的直接载体。道德的塑造与提升,自然有赖于文化的塑造与提升。
政治学研究表明,任何政治制度都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政治制度是社会—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由于民族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政治制度也呈现纷繁复杂的态势。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由人们不同的德性,产生不同种类的城邦,建立若干相异的整体。由各种不同的途径,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追求各自的幸福,于是不同的民众便创立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政治制度。”[4]这里表明,制度实际上是文化的产物,因为任何制度都是人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精神秉性下创造出来的。可见,文化对于国家这个机体来说,犹如水分对于任何有机生命体一样不可或缺,是维系国家生命的关键,也是决定国家成长的关键。
文化创造的主体是人。任何社会文化都是在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中自然形成和发展的。文化的特性在于:“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5]然而,人是生活在共同体之中的人,其文化的创造,不仅仅是自身生活与精神的需要,而且也是共同体维系和发展的纽带。故文化既创造着个体性的一面,也创造着公共性的一面。当人们从公共性的角度创造文化的时候,文化创造的主体也就从一般的个体跃升到共同体。任何共同体为了维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通过其成员这个中介,也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其中,国家是最大、也是最有力的文化创造主体。
国家塑造文化的目的不外于两点:一是满足国家自身的需求;二是满足社会精神生活的需求。前者围绕着国家品质的提升和国家治理的需要而展开,后者则围绕着人与社会的发展对文化的需求而展开。虽然任何国家的文化塑造都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两个方面,但选择哪个方面作为出发点,不同的国家则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发展目标、发展战略以及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不同。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有其文化的塑造和发展战略,其使命不仅仅在于推进文化本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在于通过文化的塑造和发展来提升国家的实力与治理水平。因为文化既是治理的资源,也是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国家在文化和文明上拥有领先地位,也就在影响其它国家的文化或文明上拥有优势地位。这种优势不仅能够巩固和提升国家在国际空间中的地位,而且能够反过来实现对自身内部社会的有效整合。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今天的国际关系学者把文化看作是国家的“软权力”。
约瑟夫·奈把权力分为两种:一是硬权力;二是软权力。奈指出了多种影响他人行为的方式,如威胁和奖励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通过吸引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前者运用的是“硬权力”,后者则是施展“软权力”的表现。在奈看来,“硬权力”指的是与军事、经济力量等具体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权力”;“软权力”则指与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硬权力指通过威胁或者奖励的方式使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软权力则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使他人自愿追求你所要的东西之能力。
软权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文化的吸引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三是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四是文化的生产和向世界输出的能力。[6]很显然,软权力的核心就是文化力量。“软权力”是在国际比较中提出的概念,反映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的文化力量,其强弱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战略地位、影响力以及由此所构建该国国际安全体系都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可见,对于国家来说,文化塑造能力直接决定着它在国际竞争中的势力和地位。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国际上的战略优势越大,其国内治理所拥有的合法性基础和相应的整合力就越强。因此,这种软权力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竞争力,它还带来对国家内部的整合力。国家对国家的影响尚且能够通过软权力来实现,国家对社会、民众的作用无疑更可以通过软权力来实现。当然,在国家内部,软权力不是体现为国家对社会所具有的文化优势,而是体现为国家通过积极的文化塑造以提高国家在文化层面上的影响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社会动员和整合,还是制度运行和效能,都离不开文化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经济学家的认识往往比政治学家更加全面、直接和深刻。美国学者斯特斯·林赛明确提出:“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机会的看法。”“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因为它们影响人们对进步的想法。文化价值观之所以重要,尤其是因为它们形成人们组织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而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有进步。”[7]经济和社会进步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文化对经济繁荣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作用,决定了国家如果要创造有效的治理,就必须高度重视文化所具有的功能。
可见,无论是国家的外部生存还是内部治理,文化都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和意义。任何国家治理都必须有相当雄厚的文化基础。文化资源与文化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文化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作用,是通过人的思想和行动来实现的。国家要借助文化来创造有效治理,就必须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其一,不断提高文化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以提高文化的水平及其核心价值的影响力;其二,不断通过意识形态的机制、文化的教育和传播,扩大文化的影响,深化文化对公民精神和心灵的塑造,创造国家共同的理想和精神。这两个方面的努力是不可分的,没有前者,后者就成为无源之水;没有后者,文化就无法发挥效应,并得以扎根成长。
三、文化整合和塑造促进软治理的发展
应该看到,文化的特殊价值和功能决定了国家进行文化塑造的过程,实际上这也是国家实现治理的过程。这种治理是从人的心灵出发,通过心灵的滋养、精神的提升和心智的开发来调节和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规范人们的基本信念和原则。这种治理基于文化这个软权力的形成,可以视为一种“软治理”。
必须强调的是,“软治理”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教化的过程,而是通过文化的塑造来提升和促进社会治理的过程。这种治理将文化、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并彰显文化发展,强调通过文化塑造和文化整合来优化人们的认同取向与认同结构,提高权力、制度与组织的认同基础,从而为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提供积极的推动力和支撑力。在这种“软治理”中,传统的意识形态教化依然起作用,但不再是基于国家对社会的权力优势,不再基于思想和价值的教条化和垄断化,而是基于文化生活与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有机结合,基于思想、价值和言论的自由。实际上,通过简单的意识形态灌输所形成的治理,本质上还是“硬治理”,因为它实现的力量还是权力,文化的要素只不过是这种权力的伪装。
对于文化塑造而言,国家为了自身的合法性,都会创造一定的意识形态,并努力使其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文化发展来说,这种意识形态的塑造就是一种文化的塑造。改革开放前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结构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诸如人民公社、计划经济甚至公有制企业的经营方式,实际上都属于政策主张的领域。然而由于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者的“重叠”,这些政策主张同时也是作为价值理想而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这种“合一”状态使得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变得集中化、单一化、僵硬化,同时表现出教条性、排它性、封闭性。所以,要使主导意识形态实现文化塑造,首先是要提炼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可以凝结为最高理念和终极价值的东西。这些“最高理念”或“价值理想”与“具体结论”不同,它具有终极性和稳定性,是主导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核心。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要逐渐摆脱“自然奴役”和“社会奴役”、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通向“自由王国”等价值理想,都具有“最高性”和“终极性”,都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高理念”和“价值理想”。 [8]其次是给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以广阔的创新和发展空间,包括借鉴传统文化中有益的部分。再次是要把“最高理念”和“价值理想”作为理论创新、制度设计、政策实施和舆论导向的出发点、原则和归宿,既不能把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混同为“最高理念”和“价值理想”,也不能使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偏离“最高理念”的价值导向。
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塑造,还是文化整合的推动,都必须建筑在对既有文明命脉的尊重和肯定基础上,即积极地正视既有的传统文化和文化基础。可以肯定地说,国家任何形式的文化塑造,首先要尊重传统,这种尊重既能保障既有的文化资源发挥作用并使文化获得新的发展,也能使有关的认同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扎根在具有共同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社会之中。在这种无声无息、但却诚心诚意的尊重中,国家的治理将获得巨大的资源和力量,从而创造出有效的软治理。
具有文化整合意义的国家文化塑造一定是在既有文化资源基础上展开的。这种塑造一面取决于既有的文化资源以及文化特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国家进行文化塑造所必需的文化能力、文化体制和文化产品。文化能力,即国家通过文化能力铸造社会核心价值、引导民族精神方向、整合社会认同取向以及培育合格国家公民的战略水平与行动能力。文化体制,即国家管理文化创新、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维护以及文化服务的体制与机制。文化产品,即在国家的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下,文化生产所形成的各种作品。对于国家的文化塑造来说,这三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能力的高低、体制的健全直接影响到文化产品的质量与水平。在现代国家,国家治理不得不立足于文化的塑造和文化的整合。所以,国家的文化能力、文化体制以及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也就成为实现软治理的基础与机制。当然,与核心价值的分配、文化基因的传承关系最为直接的教育和宣传,也是软治理得以进行的重要途径与机制。
必须强调的是,通过认同的力量所形成的软治理,实际上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直接影响国家治理所必需的组织和制度的建设。因为一种认同的形成对于治理来说具有双重效用:一是提升了认同对象(如公共权力、国家制度和公共部门)的合法性基础和权威力量;二是强化了认同主体(如公民)的社会和角色意识,从而使这些主体能够在既有的体系中行动。这种双重效用能够产生相互促进、相互深化的效果。因此,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在我看来,在建构社会时,每一种认同建构的过程都会导致一种独特的结果。合法性认同产生公民社会,也就是产生一套组织和制度,以及一系列被结构化的、组织化的社会行动者,这些社会行动者同时也再生产出合理化其结构性支配来源的认同,尽管有时是以一种冲突的方式。”[9]显然,基于认同所形成的软治理既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力量,也是支撑国家治理的内在力量。
总之,国家在创造文明社会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文化塑造过程,同时也是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过程。将文化塑造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使国家治理立足于文化塑造之中,应该是民主时代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战略选择。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
[1]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Trans. by Wu Ruiren.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ublisher, 2005p6.
[2]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55.
[2] Ferdinand Tonnies. 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Translated by Lin Rongyuan. 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99pp52-55.
[3]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40-343,364
[3] [4]Aristotles. Politics. Translated by Wu Shoupeng. 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83pp340-343,p364
[5] [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
[5] E.B.Tylar.Pritimive Culture. Trans. by Lian Shusheng.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2p1.
[6]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2-5.
[6] Joseph Nye. 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of World Politics. Translated by Wu Xiaohui and Qian Cheng. Beijing:Oriental Press,2005.pp2-5.
[7]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407.
[7] Samuel Huntington, Lawrence E.Harrison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Trans. by Cheng Kexiong. Beijing:Xinhua Publishing House,2002p40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89.
[8] Marx and Engels.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Vol.39.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74p189.
[9]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灵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
[9]Manuel Castells. The Power of Identity. Translated by Xia zhujiu and Huang liling.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p4.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上海 200433)
Soft Governance:Cultural Function in the Process of State Governance
Fu Chun
[Abstract]The main purpose of nation-state is to coordinate conflicts and create social orders by means of using public power. So on the basis of institutions, people found the nation-state to make the public power work effectively.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tate govern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tates, the promo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ulture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is democratic era, integrating cultural shaping with state governance while melting state governance into the cultural shaping, will certainly to become 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any country who wants to realize effective governance.
[Key words]soft governance, culture, state governance
[Author]Fu Chun is Ph.D of laws, Lecturer at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