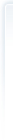
[摘要]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各种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高发频发的态势,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当前群体性事件尽管表现形式各异,但最终的指向都是政府特别是事发地的基层政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有些基层政府应对能力的明显薄弱与不足。基层政府应当从多方面来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综合治理,努力实现标本兼治。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基层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D035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09)06-0118-06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敏感时期,在面临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其中,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与公民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双重交织,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突出的社会问题。由于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最初都发生在基层,所以处在第一线、直接面对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政府(本文主要指县、市、区和乡镇、街道两级政府),就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它们的应对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可以说,切实加强基层政府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建设,不仅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也是有效提升我国政府执政能力的紧迫任务。
一、 现阶段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和基本态势
目前国内理论界对群体性事件的理解是多义的,往往因为学科视角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阐释。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群体性事件是指在特定情景下,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特定群体或偶合群体,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或表达某种诉求,或发泄不满情绪,采取超越国家法律法规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的集群行为。
依照上述定义,可以把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大致分为权益维护型和情绪发泄型两种。权益维护型事件亦称维权事件,是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从现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此类事件约占全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80%以上,其中又可以具体分为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及市民维权。[1]这种事件发生是因为政府和其它组织的某些不公行为妨碍了事件主体自身权益的实现和保障,事件主体在没有其他较好的利益诉求渠道的情况下,便以自己对社会公平的理解和方式去抗争,成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情绪发泄型事件是近些年才凸显出来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这些事件参与者的自身权益并没有受到直接侵害,只因某些偶发事件激活了他们心底郁积已久的愤懑和不满,于是借机宣泄,以实现对政府的某种意愿表达。尽管他们的参与更多是为了表达和发泄某种情绪,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心理失衡和 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公信力的质疑,容易引发政府合法性危机,其后果和影响力尤其需要加以关注。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现实中的许多群体性事件往往是上述两种类型的交织与混合。
与20世纪80、90年代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相比,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若干新的特征和发展态势:
从发生数量看,呈现出阶段性高发频发的趋势。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从1993年至2003年这10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5倍;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人数平均增长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起,增长4倍。[2]另据《瞭望》新闻周刊披露,群体性事件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3]可见,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在加快,规模在逐步升级,已经进入了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和多发期,意味着社会矛盾碰头叠加,社会风险因素增多,社会安全形势复杂严峻。
从参与主体看,愈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群体性事件数量和规模扩展的同时,所涉及的行业日益增多,已经波及到各个省、区、市的许多城市、农村、机关、学校、医院、厂矿企业等区域和组织,参与主体包括在在职和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农民、个体业主、教师、学生、复转军人乃至公务员等各阶层人员,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社会成分复杂,其中大部分为弱势群体成员。应当关注的是,近年来有些地方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即群体性事件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也没有切身利益关联,只是借机表达和渲泄一种情绪。
从涉及领域看,大多集中在农村征地补偿、城市拆迁安置、企业改制、欠资纠纷、军转人员安置、涉法涉诉、环境污染、灾害事故、社会保障等比较敏感、社会关注的几大领域。另外,这些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城郊结合部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大量的土地征用、房屋出租、商品房建筑质量、物业管理等引发矛盾剧增,再加上各类工程建设和企业发展吸引了大量来自各地的务工人员,因各种利益冲突导致的社会纠纷层出不穷,因而城郊结合部往往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地。
从组织程度看,组织化倾向日益明显。除了少数因偶发因素聚众闹事属于自发松散型事件外,多数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日益突出的组织化倾向。事件的聚散进退直接受组织者的控制和影响,尤其是一些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的事件,一般在事前或事中都有较为周密的组织、策划。这些事件的组织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自发群体行为为主的自我集体行动。这类行动的组织者一般是事件当事人,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政策水平,社会声望较高,有一定的号召能力。其集体行动方式往往采取制造社会骚乱或聚众向党政机关和厂矿企业施加压力,属于超越体制之外的政治参与形式,具有合理不合法的性质;另一类是通过正式组织及其领导出现的集体行动。这类事件的组织者往往是正式组织的成员,强调“遵纪守法”,坚持以合法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属于体制内的政治参与行为,具有合理合法的性质。有些组织者选择敏感时间来制造事端,在行动中统一口号和着装,打出标语,散发传单,极力造势向政府施加压力。此外,通过网络串联已成为近年来群体性事件聚集的新方式。个别利益诉求者通过在网络上发帖来聚集人员,倡议利益相关者在约定的时间、地点聚集闹事。这种通过网络方式聚集的事件组织者,信奉信息时代网络力量,利用互联网进行蛊惑、煽动,甚至以此寻求其它媒体的关注,尽量扩大事态,以期达到尽快解决问题之目的。
从冲突形式看,对抗性程度逐渐加剧。现在冲突的焦点已经由公众之间逐步向公众与党政机关和企业组织之间转移。有些公众抱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态,越来越多地采取了诸如冲击党政机关、堵塞公共交通、群体上访、示威游行等偏激行为,甚至采取打砸抢烧等暴力手段,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施压,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和重大人员财产损失。这种附加了对抗性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妨碍了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具有明显的违法性质。与此同时,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即在暴力程度加剧的同时,和平、理性的表达方式逐渐显现。与那些激烈的冲突方式相比,诉求者通过“非暴力不合作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一定的克制和理智,希望通过谈判、协商、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争取合法、正当的权益。
从诱发因素看,大部分群体性事件是由于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差别、利益矛盾而引发的,利益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大量事实表明,很多事件的起因涉及一些人的切身利益,而且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极易引起社会同情。如果其诉求得不到妥善及时解决,加上个别地区和单位领导在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不当,致使参与者产生怨气,从而引发过激的群体行为。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心态失衡是造成群体事件的重要诱发因素。现实生活中,有些事件的诱因看似简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事发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它是当地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累积的结果,是当地有些政府部门不作为、乱作为的必然产物。“一件普通交通事故,一起简单刑事案件,甚至于一句为壮胆而胡编乱造的谎言都可能酿成一场群体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发泄,这种对社会、政府和现实不满的心态可能比群体性事件本身更可怕。”[4]
从处置方式及手段看,由于基层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相当有限,普遍表现出“不适应症”,处置失当的例子比比皆是。许多基层政府和组织在冲突发生之初重视不够,往往错过最佳处理时机,是一种“体制性迟钝”,即走入“起因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的怪圈,从而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它集中暴露基层政府应急能力的薄弱。[5]当然,从近期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看,有些地方政府的处置能力有所提高,无论是处置思路和处置方式都有了明显的改进,取得很好的社会效应。特别是针对那些以和平、理性的表达方式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当地政府和警方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理解、宽容和克制,最后以官民互动的温和、协商的方式平息了事件,化解了矛盾和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从事件性质和演变趋向看,尽管现阶段诸多冲突中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但大量的、占主要地位的是属于人民内部范畴的各种矛盾。体现在现实中的各种群体性事件,一般不涉及社会核心理念,当事人的要求大多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并不具有反对社会政治制度的目的,也极力避免被贴上“对抗政府”的标签,所以一般属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非政治性的特征。但必须注意的是,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乏有各种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插手、煽动和挑拨,呈现出“寻求体制外解决问题”的倾向,特别是有些境外政治力量试图利用群体性事件造谣污蔑、恶意炒作,攻击中国政治制度,丑化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有些事件性质具有变异性,可能出现由非政治性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存在着有些重特大群体性事件演变为骚乱、暴乱和社会动乱的可能性。
二、理性看待当前的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群体性矛盾的外在表现,是社会关系不协调、不和谐的一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反社会行为,它能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打破社会活动的有序性和社会关系的协调性,使社会生活处于波动之中,进而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特别是那些以高破坏性的形式表现出的群体性事件一再发生,具有很大的负面效应,可能造成非理性的冲动情绪在不同的群体间传递,引发强烈的社会动荡,甚至动摇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持续威胁。正因为群体性事件与政权之间的密切关联,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贝辛格在其著作《民族主义动员和苏联的解体》中,通过收集前苏联从1987年到1991年发生的所有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发现导致苏联解体的最初原因就是接连不断的群体性事件。[6]这种情况,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
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根植于我国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时代背景之中。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敏感发展阶段,处于一种“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的并存时期。从总体上说,我国社会是和谐的,但由于我们过去片面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以致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并由此激化为群体性事件。况且,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社会存在社会冲突是正常现象。和谐不在于无冲突,而在于冲突在什么范围内、以什么方式来解决。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是客观趋势,因利益矛盾而引发冲突乃正常现象,再加上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还不成熟,政治体制改革还未完全到位,利益分化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混杂交织,这些就必然使各种群体性事件处于一种阶段性的高发频发态势。可以说,“改革开放在释放社会生产力的同时,逐渐形成了多元社会利益的并存格局,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和多元利益意识的发育,造成了各种利益之间分庭抗礼的格局,并愈益趋向于采取公开博弈方式,以致于出现了诉诸公民集体行动的态势。这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一种常态和常规,它在彰显社会活力、提示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提供了各自利益表达和实现的非行政性管道,而拓展了各自利益的可能性空间,也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了另外一种可欲的机制。”[7]对此,要有一种敢于面对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勇气,那些试图对事实真相加以掩饰、扭曲的行为都无异于掩耳盗铃,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只有正视问题,迎难而上,才能获得化解矛盾的主动权、赢得公众的认可。
现代冲突理论认为,群体之间和群体内部既有和谐与一致,又有矛盾与冲突;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既有消极、破坏的负面作用,但也有增强群体适应性、促进群体整合的正面作用。对于群体性事件,我们既要看到它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负功能,还要看到它对推动社会整合和社会进步的正功能。因为,它不仅反映了现代社会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公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而且还能释放出长期积聚的社会能量,使那些心理失衡的公众得以实现心理上的平衡,从而有助于调养社会身心,释放社会紧张,起到一种社会安全阀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政府管控社会风向标和警报器,能表明社会上存在着某种利益的分化和失衡,表明有部分群众存在着利益诉求和对政府、社会的不满,表明政府的调节机制出了故障,甚至暴露出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基层组织社会控制能力的不适应,从而提醒政府根据这些信号,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矛盾的化解,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暴露出的社会矛盾比藏而未露的隐秘性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危害有时更为可怕。[8]
其实,对于目前的各种群体性事件,除了极少数具有阶级性、敌我性外,基本上是属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常规性的公民集体行动,换句话,它是一种社会常态。而且可以预料,今后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的加剧以及民主政治生活的扩展,此类公民集体行动有可能越来越多发生,规模也有不断升级之势,并可能出现更多趋于理性、平和与有序的行动方式。对此,需要新的开放思维来加以认识,认真把握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一般规律。既要摒弃过去那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又要谨防胡乱定性,把一般性事件盲目上升到“政治高度”,把群众利益诉求“泛政治化”,要么认定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要么认定是有“黑恶势力组织操纵”,进而用专政手段对待参与者和围观者,人为地把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对立起来。这种思维和做法是需要认真反思并极力加以避免的。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现阶段社会条件下,群体性事件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它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
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经验表明,公民以和平方式表达集体诉愿,以公开博弈争取社会理解,以集体行动与利益同对方和政府进行沟通,甚至于向政府施压,实际上是一种让社会不同诉愿和平释放,理性对话,从而建设真正平安和谐社会的有效形式,也是一种社会成本较低的利益实现机制。各种游行、请愿行动几乎无日无之,不仅不是社会动荡、秩序崩解、四分五裂的征兆,相反,经由释放诉愿和表达不同主张,利益摩擦造成的社会紧张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或者缓解。将冲突和裂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求得程序性解决,从而重新配置资源与利益,将失衡的正义校正过来,恰是医治社会疾患、建设和谐人间的较为不坏的选择。这是发达国家早己验证了的社会治理经验,也是有关民主政治的法理常识。[9]
三、群体性事件凸显基层政府应对能力的薄弱与不足
透视近年来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导火线不同,但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大体雷同。那些颇具影响力的事件,几乎无不是由群众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政府部门对群众的合理诉求麻木不仁、有些领导干部违法违规行政甚至贪赃枉法、不恰当使用警力激化矛盾等所造成的。尽管其表现形式各异,但最终都指向政府特别是事发地的基层政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有些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的明显薄弱与不足。
法治理念淡薄,法律手段缺失。毋庸讳言,当前各级政府对群体性事件都是高度重视的,都要求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认真做好各项预防处置工作,但许多基层政府干部往往不能从法治的视角来理性认识、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过分依靠政治手段来处置,有的甚至一有群体事件,就用堵的办法、高压的措施来应对,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后果。与此同时,目前我国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立法和法律建设方面仍存在诸多缺陷和误区,譬如,如何科学界定群体性事件?如何正确区分群体性事件与公民自由表达权的行使方式,进而妥善、合法处置群体性事件等,还缺乏清晰的法律条文。另外,至今尚没有一部全国性群体性事件处理的专门法律,以致执法机关不能很好地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合法与否作出准确判断,甚至有些执法机关在处置过程中出现了执法犯法的现象。
角色定位出现偏差,公共权力行使方式欠妥。现代政府的角色定位,应如著名行政学家罗伯特·登哈特所说:“服务而不是掌舵”,应该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能够公平、合理地处理利害相关者的矛盾和冲突。但现实中有些基层政府的决策随意性大,对涉及拆迁征地、企业改制、移民安置、收入分配等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常常是暗箱操作,不尊重民意,而一旦出现事端,又怕承担责任,能捂则捂、能压则压、能拖则拖,千方百计掩盖事情的真相。还有些基层政府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博弈中严守“政府中立”原则,反而把自己和强势集团捆绑在一起,“执政为民”的宗旨被异化为“为老板服务”、“为资本服务”,漠视了群众的正当权益。更有甚者,有的基层政府官员把自己当作商人,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与民争利,追求垄断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状况,必然是官官相护、官商勾结,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和公平正义法则。
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压制和扭曲社情民意。在当今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分层加剧的情况下,需要建立有效的利益沟通协调机制,使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得以有效整合,特别是当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受损而又不能得到公正解决时,可以通过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沟通与协商渠道来寻求救济。但事实上,由于一些基层政府出于“政绩”需要或地区、部门、个人利益考虑,不惜采取欺上瞒下、堵塞言路等手段,压制社情民意,使得群众利益诉求意愿难以实现,弱势群体的呼声无法及时反映到上级政府那里。于是,一些群众为了自身的权益,容易采取过激过火行为,甚至纠结起来通过越级群访等形式发泄不满情绪,酿成了重大群体性事件,进而使社会公共秩序受到危害。
预警和应急机制不健全,现场处置不力。现代社会的预警机制至关重要,它是对社会运行状况发生信号,显示社会已经或即将发生无序现象的临界状态,以致引起社会管理者和社会公众的注意,及时采取对策,使社会运行状况不再继续恶化的一套制度和方法。[10]建立预警机制的意义在于形成一套快速反应的应急体系,以便为科学决策所必须快捷获取信息奠定必备的基础。但从现实情况看,很多地方的预警和应急机制还很不完善。由于种种原因,对群体性事件不报、漏报、瞒报、迟报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有些官员为了逃避责任追究,想尽各种办法不让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知道下面的真实情况,以致那些根据不实信息建立起来的预警机制无法发挥应用的功能。在现场处置方面,相当一部分基层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水平相当有限,许多本来在初始阶段就能化解的矛盾,由于处置不当或判断失误错失了良机,使事件大大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应有的严重后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基层政府及其干部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危机公关意识相当薄弱,与现代信息社会所要求的媒体应对能力极不相符,丧失了掌握信息、引导舆论的主动权,使得谣言凭借现代传播工具呈规模效应模式不断扩散,那些不明真相而又义愤填膺的群众迅速被高度情绪化的传言动员起来,容易产生“共振”效应,直至酿成了群体性事件。
有些基层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导致矛盾激化升级。目前有些基层政府存在的违法乱纪、执法不公、官僚主义现象,集中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漠视群众利益、听不进群众意见、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衙门作风,已经引发了群众的对立情绪,使一些基层政府失去了应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那些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地方不难看到,有些干部对事关基本民生问题乃至生命安全的大事,往往视作“小事”,马虎应付,草率处理;面对那些错综复杂而又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的不敢管不愿管,明哲保身,或者避重就轻,逃避现实。此外,当前在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和利益纠纷时,有些基层政府过度依赖于采取强制措施,甚至随意动用警力,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这不仅不利于缓解和消除矛盾,反而不断制造矛盾,加剧了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用专政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尽管从表面上看事件是平息了,但怨气却不断积累,不满情绪在潜滋暗长,可能为日后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四、加强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建设的建议
不可否认,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在治理群体性事件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有能力对一些突发事件进行应急管理。但是,应急管理能力的提高并不表明能够消除产生大规模社会危机的根源,管理危机与消除危机根源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如前所述,当前群体性事件根植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其深层次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由此也凸显出基层政府在应对能力上诸多方面的薄弱与不足。正是基于此,处于直接面对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政府应当采取综合治理的对策措施,切实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努力做到标本兼治。
首先,规范基层政府行为,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当今众多群体性事件的矛头最终都指向了政府首先是事发地的基层政府,基层政府往往成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关键当事方,成为事件的最大风险所在。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职能定位、制度建设、管理方式以及治理能力上存在的不适应性。对此,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应认真审视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职责旅行方式,把群体性事件作为自身治理变革的一个契机和转机,切实转变公共管理理念,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换,积极改进行政管理方式。由于我国原有的政府管理模式基本上以政府为本位,很多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都是以方便政府管理的原则设计出来的,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为市场竞争、社会发展提供规划和维护秩序的服务者,所以,必须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政府与企业、公民的关系,规范权力运行,主动回应公众的关切和诉求。要大力推动从管制型基层政府和服务型基层政府的转变,建设公开透明的公共财政,保证财政投入向公共服务倾斜,缓解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公共需求凸显与公共服务不足的矛盾,努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要稳步改革现有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和单位体制,避免公众之间和公众与所在单位的矛盾冲突演变上升为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保证政府能以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平正义仲裁者的角色出现,防止执法不公、与民争利,形成基本和谐的官民关系。
其次,完善基层政府决策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冲突。事实表明,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集中表现为各种经济利益冲突,不少群体性事件都是因为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和重大改革考虑不周或估计不足而引发的,其中不乏因决策失误、政策不当而激起民怨的。可见,改革和完善基层政府决策制度,切实将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结合起来,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水平,是基层政府转变公共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政府决策要更好地体现公众利益,必须有严格、系统的制度作保证,当前尤其要突出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性,努力实现从权力决策向民主决策、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从部门决策向公众决策的转变,对于那些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可能因实施产生利益冲突的重大事项、改革举措,都应建立安全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凡是得不到大多数群众理解与支持的坚决不施行,只有经过评估得到大多数群众认可的方案才付诸实施,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
第三,加强法治建设,规范公共参与行为。当前群体性事件可以归结为转型社会中的参与性危机,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转型社会公众参与的特殊性。一般地说,公共参与作为公众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影响和改变政治过程的活动,是一个国家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但在转型社会,由于缺乏系统而规范的公共参与准则,非制度的公共参与大量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公共参与的积极作用。[11]为此,要在充分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上,对公众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和途径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同时,要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和素质,教育公民在维护合法权益时,不得妨碍国家、集体和个人权益,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平和的方式表达诉求,逐步减少具有破坏性的群体性事件的表达方式。
第四,建立政府主导的维权机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其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12]由此可见,建立合理的民意表达机制显得十分重要。在社会利益格局激荡变化中,要着力构建体制内力量为主导、兼顾多元主体的维权新机制,建立健全畅通有序的利益表达渠道,及时沟通政府与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努力协调和规范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避免具有破坏性的利益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各个利益主体在政府主导和适当干预下,通过相应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彼此之间提出利益诉求,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协调解决矛盾,努力把各种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取缔非法的利益获取渠道,满足正当的利益诉求需求,对利益受损者给予合理的补偿,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保障,从而使利益关系趋向合理化,最终形成一套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利益分配体系。
第五,提高舆论引导水平,把握新兴媒体建设和管理的主导权。当今信息时代,网络和媒介形式为人们提供了表达诉求、提出建议、发泄紧张或不满情绪的重要载体,它对社会发展具有监测和引导作用,能够把握社会心理走向,实现人们不满情绪的有效舒解。因而,基层政府应学会与媒体打交道,不断完善群体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应急工作机制,充分保持对信息舆论的敏感性,努力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善于借助媒介力量获取和提供有效的信息,并通过媒介积极引导舆论,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危机公共策略。随着我国手机用户和互联网用户的急剧增加,当前特别要发挥新兴媒体在教育、引导、塑造和谐心态与健康人格等方面的作用,准确把握网上舆论态势,避免出现庞大的“不明真相”的旁观者,防止社会崇尚的价值观与政府主导的价值观的错位与悖离。
第六,改进干部绩效考核办法,完善以官员问责制为主的责任追察制度。诚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具有多方面因素,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自身工作存在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并改进工作作风,以官员问责制为主的责任追察制度逐渐形成。但必须看到的是,由于有些群体性事件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不管什么原因,都把这些危机的发生与政府部门的绩效、与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挂起钩来,则有失偏颇,也不利于政府官员在其职责范围内勇于担当,不上交问题而转移责任。所以,不应当把事件发生与否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而应当把如何预防事件及事件发生后行政官员的行为作为其考核指标。当然,如果政府部门及官员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
第七,加强应急管理培训,切实提高基层领导者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是一项综合能力,其能力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能力建设。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要把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应急管理的知识和技能培训,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班和培训班,切实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制定公共政策能力、协调利益冲突能力、处理公共事务能力、开展群众工作能力、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媒体应对能力、现场处置能力等,认真把握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规律,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及时解决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为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奠定基础。
第八,借鉴国外经验,掌握现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原则和策略。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曾经历过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高发的年代。多年来,这些国家逐渐摸索出应对、处置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一般原则和策略。我国有关专家在此基础上,通过长期的观察研究认为,从微观情景看,执政者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抗议的要点在于:在介乎“妥协”和“压制”之间的灰色地带中拿捏的尺寸。[13]大致说来,应把握的原则和策略:一是主要负责人应第一时间亲临现场、靠前指挥;二是将参与者和旁观者分隔开来,以免人员混杂,出现更大范围的秩序混乱。三是保持信息畅通和公开。在黄金24小时内公布准确、真实信息,避免不良消息的传播扩散;四是慎用警力、警械和强制措施,严防因用警不当、定位不准、处置不妥而激化矛盾;五是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对理性、和平的非暴力行为一般持宽容和克制态度,而一旦出现违法犯罪行为则必须果断处置,迅速控制事态,同时注意把握好分寸,避免操之过急或过大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1).
[1] Yu Jianrong. People’s Venting Their Anger upon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Governance. 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 , 2008(1).
[2]汝信等.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35.
[2]Ru Xin.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China's Development [2005].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4 , 235.
[3]“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号[J].瞭望新闻周刊,2008(36).
[3] The Alarm of “Typical Group Events” .Outlook Newsweek, 2008(36).
[4]孙元明.当前国内群体性事件及其发展趋势研究[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8(3).
[4] Sun Yuanming. Domestic Group Events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s. Journal of Jiangnan Social School, 2008(3).
[5]群体性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应急和对策[J].领导决策信息,2008(28).
[5]The Emergency and Response of Groups with No Direct Interest Conflict. Leadership Decision-making Information, 2008(28).
[6]郑永年.中国越来越多社会群体性事件表明什么?[EB/OL]www.tecn.cn/data/detail.php,id=4671 31K 2009-3-13.
[6]Zheng Yongnian. What Do the More and More Chinese Group Events Indicatewww.tecn.cn/data/detail.php,id=4671 31K 2009-3-13.
[7][9]许章润.多元社会利益的正当性与表达的合法化[J].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7] [9]Xu Zhangrun .On Justice of Diversified Social Interests and Legitimacy of Those Interests Expression.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8(4).
[8]叶国兵.用和谐理念指导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处置[J].公安教育,2008(4).
[8]Ye Guobing. Guide the Prevention and Disposal of Group Events With the Harmonious Idea. Police Education, 2008(4).
[10]丁水木等.社会稳定的理论与实践[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282-283.
[10]Ding Shuimu et al..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ress, 1997pp282-283.
[11]缪金祥等.社会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理性分析[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6).
[11]Miao Jinxiang et al.. The Analysis of Rural Group Ev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Journal of Shandong Public Security College, 2005(6).
[12]赵守东.群体性事件的体制性症结及解决思路[J].理论探讨,2007(2).
[12]Zhao Shoudong. The Institution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to Group Events.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2007(2).
[13]单光鼐.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学问[J].瞭望新闻周刊,2008(36).
[13]Shan Guangnai. Disposals of Group Events. Outlook Newsweek,2008 (36).
(作者单位:福建行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福州 350002)
Managing the Group Even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apacity-building of Governments at Basic Level
Xiao Went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