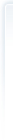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070)、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项目、南京大学“985”三期文科改革型项目“社会治理的历史与逻辑——走向服务型政府的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本文根据问责方偏好与组织使命的吻合程度和问责方对负责方的强制程度,为非营利组织问责提供了一个新的分类——自我问责、层级问责、社会问责、法令问责。问责成本可以分为狭义实施成本和机会主义成本,其中实施成本随吻合程度或者强制程度的上升而上升,机会主义成本随吻合程度或者强制程度的上升而下降。问责类型的选择和组合主要是一个成本权衡的问题,不同情境的最优问责有匹配的吻合程度和强制程度。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问责;实施成本;机会主义成本
[中图分类号]C23; D035.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12)07-0104-06
一、引言
受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和慈善总会虚开发票等事件的影响,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的问责议题正在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值得学术界和实务界深入关注的是,NPO有各式各样的利益相关者,相应地有各式各样的期望和问责,这些不同类型的问责可能相互冲突,所以存在对不同类型问责的权衡取舍问题。比如赞助人希望NPO高效地使用每一分资金,但这可能阻碍服务对象在生活质量等方面获得实质性的改善;社会和公众希望NPO公开各种信息,但公开信息是需要投入的,不排除会挤出其他更重要工作的可能;政府监管部门希望NPO安分守已,但NPO为践行使命需要不断创新,等等。而且,事实问责不一定就是好的,比如自利的赞助者凭借资源优势套取不当利益,谋求点击率的网站因发布虚假信息而给当事NPO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不适当的政府监管加重NPO负担,等等。因此,NPO问责本身就有对其适当性、正当性的判断问题。上面这些问题在累积的研究文献上都没有得到过系统、圆满地解答,现有相关研究成果还主要停留在范畴、框架、分类等的初步探讨,以及一些个案研究和描述研究,缺乏深入的、抽象的、可在经验上验证的理论演绎。因此,学术界和实务界迫切需要为NPO开发一些一般化的理论,来为不同问责的取舍和问责适当性的判断等提供依据。本文拟在评述NPO问责已有分类的基础上,借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和“契约”概念,提出一套新的、适于进行成本分析的分类标准和问责类别,以期望为NPO的问责选择和设计提供可能的指导依据和参考意见。
二、分类述评
NPO的问责分类可谓是数不胜数。[1][2]李勇提出了一个法学意义上的政治、法律和目标分类[3],不过类似分类在实务操作中都有交叉重叠,政策和管理的含义不是很清晰。康晓光和冯利的积极和消极分类倒是具有一定的政策和管理含义[4],但他们没有继续探讨各种问责的优劣与适用情境,而且他们过于简单的分类也似乎不足以应付复杂的实践。再有其他更常见的分类,像内部、外部问责,向上、向下问责,事前、事中、事后问责,等等,就都似乎局限于识别的价值,很难为实务操作提供更多、更深入的启示。
最早从政策和管理上来思考问责类型的应该是Kearns,他根据外部命令的清晰与否和内部反应的积极与否区分了四种问责:商谈型、遵从型、专业型(自由裁量型)、预期型(定位型)。[5]该分类在今天看来是模糊的:像商谈型,在非营利领域恰恰是很多都带有明显的积极性;还有遵从型,不少时候负责方需要服从于权力和权威恰恰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再有预期型或者定位型,如果标准明确,恐怕也难有积极的战略性价值。而且,该分类在更多意义上是事后适应性的,而非前瞻设计性的,即根据似乎不能更改的问责要求来决定负责形式,而非根据一些更加外生的因素,来设计匹配的问责模式。
NPO应用最多的问责分类来自于Romzek和Ingraham的公共部门研究,她们根据控制来源和被控方的自主程度将问责分为四种:层级型、法律型、专业型、政治型。[6]该分类应用广泛,但并非没有缺陷。首先是分类标准的问题,两个标准分属于不同行动主体,容易产生交叉重叠或者遗漏的问责。比如专业问责,相对于组织成员来讲可能是来源于组织外部的专业协会,同时对于个别主体来讲,也不一定就是自主性较高的,个人忍受专业煎熬、专业标准超越法律条款都是常有之事。其次是控制范畴的问题,控制属于“前治理”时代的语言,用来审视治理时代的问责并不适当。其一,现代问责远远超越了控制的含义,像创新性期望在很多场合都是更加重要的,此时的控制只是相对次要的、甚至是可能被舍弃的价值。其二,问责与控制对应着不同的政治价值和管理策略,甚至存在着冲突,所以用控制来界定问责必然会引发混乱。治理时代的问责在本质上是一个相关方之间的交互作用问题,它有控制的成分,但远非强调单方向的控制主题所能引领。事后看,控制与问责有同义反复的嫌疑。事前看,可控又意味着负责方只有循规蹈矩,故问责方在事后就没有必要问责。而事实上,只有处在模糊的可控与不可控之间,事后的问责才有存在的价值。
问责研究还有一些涉及问责本身维度的区分,例如Kearns的监督、评估、反馈[7],Koppell的透明性、承担责任性(Liability)、可控性、履行职责性(Responsibility)、回应性[8],以及Ebrahim在向谁负责、问责什么、怎样问责等方面的细分[9]。对于建构一般理论有启发价值的是,Ebrahim特别区分了会员型、服务型、政策倡议型组织,认为组织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不同问责的取舍或者侧重,不过这种区分如果缺乏规范价值的指导,很容易产生组织本位主义的问题。对于问责本身维度的区分有政策、管理上的方便,可以为问责实务提供一些意见,但也使问责知识限于琐碎,可能阻碍一般化理论的建构。
总结已有的NPO问责分类和维度区分,它们共同的问题是,相关理论都还不足以系统地回答各种问责何时冲突、何时共容,以及何时选择、或者侧重于何种问责的问题,而这正是本文研究期望突破的——找到适于进行成本分析的分类标准,不仅为NPO问责提供一个新的类型学,更为实务操作中问责类型的选择和设计提供思路。
前面回顾了各种分类标准,它们的成本含义都不甚清晰。例如各种简单的分类标准,像内外、上下等,都与成本没有直接的联系。还有Kearns的命令清晰标准,可能会带来成本的下降,但相反情况同样存在,因为命令再清晰,如果本身脱离非营利使命的要求,反而会带来广义问责成本的上升。再有Romzek和Ingraham的控制和自主标准,从后续研究看,她们区分出的各种问责各有优劣,但相关优劣与分类标准没有必然的联系。[10][11]下面,我们再回顾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包含成本权衡思想的经典契约模型,以为后面的问责分类及成本探讨提供可靠的指引和坚实的支撑。
三、分析基础
问责是一种“关系”,或者用更加规范的学术语言来讲,它是一种“契约”。契约主题在经济学中最早受到科斯的关注。[12]他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交易在市场上进行、有些交易在企业内进行,给出的答案是交易成本,即哪种形式的交易成本低,就选择哪种交易形式。
将科斯学说精致化的是威廉姆森(Williamson),他将科斯的企业问题抽象为一般化的契约治理问题,治理原则是狭义交易成本和官僚成本等的权衡。狭义交易成本在根本上是源于行为主体的机会主义动机,这是比自利更甚的“狡诈”,一般是指不完全或者扭曲性地释放信息,特别是指精心设计的误导、扭曲、颠倒、迷惑和其他种种混淆视听类行为[13],同时其他因素像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和交易内容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频率等,则都影响着机会主义的治理,进而决定所有的狭义交易成本[14]。如果要分类,狭义的交易成本可以分为事前的搜寻成本,事中的讨价还价成本和决策成本,以及事后的失调成本、后续谈判成本、启动成本、运行成本和保证成本等。[15][16]为规避可能的狭义交易成本,契约方可以选择非市场的治理模式,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新治理都会产生额外的成本。比如企业,由于层级的管理模式,它在应对协调性的适应问题上是具有了独特优势,但也产生各种官僚成本,包括建立、维持或者改变一个组织设计的成本,组织运行成本,以及各种官僚主义行为的不良影响。[17][18]因此,契约治理需要权衡各类成本。比如不考虑生产成本等,仅考虑交易内容资产专用性和交易主体自主维度的影响:当资产专用性较低时,契约方还是可以选择市场模式,承担必要的狭义交易成本,但好处是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激励;当资产专用性很高时,就应选择层级模式,忍受一定的官僚成本,但关键是可以保留充分的适应手段,进而规避相对极高的狭义交易成本;当资产专用性一般时,就可以选择混合模式,规避同样都相对很高的狭义交易成本和官僚成本。[19]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学说主要发展于私人领域,在公共领域,开创性的成本权衡是政治经济学中布坎南和塔洛克的立宪模型。[20]布坎南等研究的问题是,人类为什么会加入集体组织,采取集体行动又会选择什么样的决策规则?由于人类生活的相互依赖性,个别行动主体可能不得不忍受其他行动主体带来的外部成本,而集体行动则被视为一种降低这些外部成本的可行方法。不过集体行动同样给个体强加成本,布坎南等称之为社会相互依赖成本,如果该成本低于前面那些外部成本,那么个体自愿加入集体组织,反之则不加入。社会相互依赖成本被布坎南等划分为两类成本。一是决策成本,它是个别行动主体作为决策集团一员在作出选择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个别行动主体是否成为决策集团成员是一种机遇,发生机制类似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由于人类交互活动和决策数量,决策成本随决策集团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二是政治外部成本,它是决策集团强加给非决策集团成员的成本,随决策集团规模的增加而降低。显然,假设集体行动规避的原始外部成本一定,或者说集体行动的收益一定,那集体行动的最优决策规则就是社会相互依赖成本最小的规则,而这里面的关键正是决策成本和政治外部成本的精妙权衡。冲击原来自由主义者政治直觉的是,布坎南等的权衡模型表明,没有适用于所有情境的某一决策规则。特别是所有人都同意的决策规则,恰恰在绝大多数场合都非最优,其虽然将政治外部成本降至为零,但决策成本太高了。相反,独裁却也有可能是最优规则,比如在类似决定警察穿啥颜色制服的无关紧要场合。
NPO问责契约兼具私人性和公共性特征,这使得我们可以借鉴、融合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的分析范畴与框架。首先是借鉴威廉姆森的官僚成本和布坎南等的决策成本,我们在NPO问责成本中划分出第一类的“狭义实施成本”,它是指问责方为实施问责、和NPO及其他相关主体为匹配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期望和问责,而付出的成本,具体包括相关的设立组织、创建制度、配备人员、沟通和协商、认知要求、学习技术、测度指标、回收反馈等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组织和政治等层面的部分交易成本[21],它们在价值上都是中性的,由正当的问责活动带来,是组织及相关主体因问责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NPO与一般的营利组织不同,不仅缺乏财务的底线,面临的外部竞争也有限,而且大多数工作和成果或者是属于主观性很强的内容,或者是属于复杂的技术性内容,不仅价值和成本难以计量,且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所以问责NPO可资利用的条件有限,面临的信息障碍会更多、更难以逾越,实施成本会十分突出。
其次是借鉴布坎南等的政治外部成本,也融入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内容,我们划分出第二类的机会主义成本,它是指NPO及相关主体,为规避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正当问责和不当要求而付出的成本,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因不当行为而给NPO及相关主体强加的成本。同样与营利组织不同,NPO有多类诉求各不相同的利益相关者,且每类利益相关者都可能对组织事务拥有否决权[22],所以通过突出机会主义成本,可以重点评估不同问责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及其与组织整体利益的张力。机会主义成本带有负面的色彩,脱离了问责的规范性要求,在价值上应该遭受批判,但在不完善的现实世界里实属难免。造成世界不完善的因素主要包括主观行动者的可能自利、非全知全能,以及客观事物的复杂、不确定等。典型的,管理者的自肥,对个别强势利益相关者的讨好,业绩数据的造假,以及外部不切实际的要求,赞助者和社会公众的误解,政府监管的武断,等等,都会形成或者加剧机会主义成本。
四、分类框架
从已有的问责分类看,大多数都有内部、外部的区分,这是一个问责主体的问题。不过内、外区分是模糊和复杂的。在内外之间,比如志愿者,可以认为是内部人士,但从进入、退出的角度而言,广大的潜在志愿者又是外部人士。同时在“内—内”、“外—外”之间,不同问责者与组织的整合程度也都不同,比如在公益型组织,志愿者与组织的整合程度就要强于一般赞助者。为规避这些问题,同时秉承布坎南等的立宪精神,我们抽象出第一个分类维度——问责方偏好与NPO使命的吻合程度。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如果吻合程度越高,则实施成本越高,机会主义成本越低。实施成本的含义是指,问责方偏好与组织使命越吻合,他们为组织提供的资源就越多,同时NPO及相关主体越有激励吸引问责方提供资源、或者参与工作团队、甚至直接加入组织,相应地为相关工作付出的时间和资源就越多。机会主义成本的含义是指,问责方偏好与组织使命越接近,对组织及相关主体的不当要求就少,所以组织及相关主体遭受的不良影响就少,同时组织及相关主体相关工作匹配问责方期望相对容易,逃脱问责方监管相对困难,所以组织及相关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就少。
问责分类的另一类常见标准是控制形式、控制程度、或者相反方向上的自主程度等,这些都属于问责形式的问题。控制类标准的弊端在前面已经批判,在这我们抽象出一个相关维度——问责方对负责方的强制程度,该维度可以规避控制范畴带来的混乱问题,但保留控制可能作用于问责的相关内容,而且有价值的是,该维度可以直接应用威廉姆森学说。比照威廉姆森层级与市场等治理模式的比较: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如果问责方对负责方的强制程度越高,则组织及相关主体建立专门机构、专门制度等的成本和运行成本就越高,即实施成本越高;不过同时组织及相关主体对外部的适应能力会更强,应对外部变动的调整成本更低,外部变动造成的损失更低,这些都说明机会主义成本更低。
简单在各个分类维度上作两分法,可以得到一个新的NPO问责分类,具体见表1。该分类在表面上与罗姆泽克(Romzek)和英格拉哈姆(Ingraham)的相似,但在关注的实质性内容上有较大差异。
表1 非营利组织的问责分类
吻合程度 | |||
低 | 高 | ||
强制 程度 | 低 | Ⅰ:社会问责 | Ⅱ:自我问责 |
高 | Ⅲ:法令问责 | Ⅳ:层级问责 | |
在表1 中,假定强制程度都较低,根据吻合程度,可得方格Ⅰ社会问责与方格Ⅱ自我问责。社会问责接近于罗姆泽克等的政治问责,指的是偏向于组织外的利益相关者,在没有暴力优势、或者明显其他资源优势的条件下,对NPO施加的问责。自我问责与罗姆泽克等的专业问责有交叉,指的是偏向于组织内的利益相关者,在没有明确国家法律和组织规章的条件下,凭借自己对专业知识、组织使命、社会规范等的认知、反思,而对自己和组织施加的问责。
从实施成本来讲,社会问责的成本要低:相关成本分布于社会各界,社会各界也只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投入于NPO,且从各个NPO的角度而言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等优势;NPO自己及相关主体则更多是消极性地应对,很少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机构和制度。自我问责的实施成本相对较高:问责直接增加或者影响非营利工作的投入,且相关投入具有更多专业方面的要求;同时组织整体也应该为自我问责提供可能的条件和资源,以提升组织整体践行非营利使命的能力。从机会主义成本来讲,社会问责的成本相对较高:普通公众、媒体、网站等都可能有自己的偏狭利益,非营利议题反而可能成为他们追求其他目标的手段,且外部型主体对于组织内部知之甚少,很容易有一厢情愿的要求;同时组织及相关主体也可能因形势紧迫等而迁就、甚至讨好所谓问责方,但牺牲正当的专业利益。自我问责则有相反方向的趋势,很多人士之所以成为内部人,本身就有非营利的目标,已经放弃了高薪等私益追求,同时在信息、交流等方面有优势,所以有激励,也有条件与NPO和社会的期望合拍。
以赞助者和志愿者问责为例,前者一般可以归为外部的社会问责,后者可以归为内部的自我问责。就赞助者而言,他们对NPO的关心一般只是自己生活的极小部分,同时NPO的相关工作一般只占组织所有工作的一小部分,且大多数都不是日常性的,故实施成本较少。不过由于在偏好、目标上与NPO的差异,大赞助者可能更看重税收优惠,不排除在监督有限的条件下,有强烈的动机与NPO的管理者合谋。小赞助者可能固执于每一分资金是否被浪费、或者是否直接达到受助者,却忽视现实非营利工作的复杂性[23],或者是本身就认识不到非营利工作的真正重心,像很多非营利工作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服务对象专门、持续的投入,而非借助于蜻蜓点水式地配置到捐助资金或者实物就能够实现。就志愿者而言,他们投入NPO的已经有不少时间和精力,超越了简单的金钱和实物转移,同时NPO,特别是公益型组织的志愿者工作就更占组织所有工作的很大部分,所以实施成本较大。不过由于个体偏好与组织目标的吻合程度很高,志愿者和相关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就很少,有的也影响有限。
在表1中,假定强制程度都较高,根据吻合程度,可得方格Ⅲ法令问责与方格Ⅳ层级问责,这与罗姆泽克和英格拉哈姆的法律问责、层级问责一致[24],不过我们主要关注成本含义。在法令问责中,与社会问责类似,很多工作都具有规模经济等优势,分摊到具体NPO的很少,同时NPO的相关工作都只占组织所有工作的小部分,有也主要是偶然性和被动性的,所以实施成本相对较少。不过机会主义成本可能极高,因为远离问责方,问责方也有自己更加广泛、且可能与非营利使命冲突的偏好,所以NPO可能难以适应,甚至是只能被动地接受,同时政府和官僚等问责方,也可能凭借问责行为而实施相关的滥权、贪渎等行为。比如政府自己只是简单地出台一些准入规则、业务规则和会计规则,但NPO可能承受不起随之的各种负担,严重影响正当、正常的非营利工作。[25]在层级问责,相关工作属于组织的常规工作,实施成本必然很高,不过机会主义成本很低,层级组织适应、协调能力强,本身就为处理很多复杂、多变事务而设立。
比较了吻合程度的影响,再假定其保持不变,我们就可以比较强制程度的影响了。首先是吻合程度都较低的方格Ⅰ社会问责与方格Ⅲ法令问责。在社会问责中,很多内容的强制性有限,未达标后的惩罚也有限,所以组织和相关主体的专门准备趋向简单应付就可以,即实施成本相对较低。不过由于问责内容的模糊性,问责方与负责方会有更多分歧,所以机会主义行为相对容易发生,发生了也因强制程度较低而难以纠正。而法令问责则是相反的倾向,强制性和惩罚预期使得组织有激励严肃对待,同时问责内容的明确性和问责方的强制手段也相对限制了NPO和相关主体的机会主义空间。以媒体问责和政府问责为例:在实施成本方面,前者要求对于大多数NPO来讲只是偶然性的,后者就需要NPO应付定期的登记、备案、检查等任务;在机会主义成本方面,媒体有很多操控空间,不良影响会相对突出,而政府的要求则相对明确,可变空间相对较小。[26][27]
再比较吻合程度都较高的方格Ⅱ自我问责与方格Ⅳ层级问责,这可以直接套用威廉姆森的比较:层级问责有实施成本的负担,但有处理机会主义问题的优势;自我问责有实施成本的优势,但机会主义成本在上升。
五、简单应用
根据上面的分类框架,我们可以将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责填入图1。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有两个分类维度,影响问责成本、包括两个维度的现实因素也多种多样,且不同因素在不同情境的影响还有不同权重,所以图1不指望对所有问责、甚至成本作精确排序,只是想表明问责的刻画维度、及其对问责成本的作用方向。
图1非营利组织的问责归属
考察图1中一些排列相对靠近的问责,它们的维度比较和成本比较应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例如前面没有提及的司法部门和监管部门的问责比较。前者在强制程度上更甚,如果真的被触发,会引发大量应诉成本;同时其确定性更高,相关主体只要遵纪守法,没有明显重大过失,难有意料之外的成本。后者在强制程度上差些,相关工作可以融入日常工作,作为日常工作的副产品;但确定性也差些,出台新规则、修改旧规则不是不少见,所以组织和相关主体的调整成本可能会不少,滥权贪腐等行为也更加容易发生。
还有组织、行业、政府的问责。它们在吻合程度上依次递减,故组织和相关主体的实施成本在下降。但外部性带来的机会主义成本在上升:像行业问责,可能仅是某些强势者利益的体现,甚至是出现强势者通过行业规章来打压、掠夺弱势者的现象;而政府问责可能仅是出于自己管理社会整体的方便,甚至是设租的需要,却忽视组织和行业本身的规律和复杂性。
再有组织内部的按章办事与前瞻性学习,强制程度有较大差异。前者占了组织和相关主体的绝大部分工作量,实施成本是大头。后者对于追求发展的组织来讲也不可少,但其强制性较差导致不确定性较高,事后调整也受限,所以容易诱发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甚至是促成个人退出、组织分裂、使命更改等重大变故。
除了鉴别现实生活中的问责差异,本文分类框架的最大价值是可以关注问责的成本内容,即通过对问责方偏好与NPO使命的吻合程度、问责方对负责方的强制程度之比较、测度,来解释和预测问责的实施成本和机会主义成本,进而比较和权衡这些成本,最终为NPO问责的选择和设计提供依据。
回到表1的分类框架,从吻合程度的角度来讲,法令类型和社会类型的问责因吻合程度较低而形成实施成本的优势,但其因外部性而产生机会主义成本的劣势,而自我类型和层级类型的问责呈相反方向的成本规律,因吻合程度较高而可以节省机会主义成本,但也需要付出实施成本的代价。从强制程度的角度来讲,社会类型和自我类型的问责因强制程度的较低而形成实施成本的优势,但这损失了治理机会主义行为的手段,而法令类型和层级类型的问责也呈相反方向的成本规律,因强制程度较高而形成治理机会主义行为的优势,但这也以实施成本的上升为代价。因此综合言之,各种类型的问责各有优劣,现实可行的是根据相关情境,测度相关问责的吻合程度和强制程度,以此来评估、权衡实施成本与机会主义成本,再选择经济上最佳的问责类型或者类型组合。
上面思路可以简单用图2表示:鉴于NPO问责的广泛好处和公共性,假定问责好处相对固定,则最优问责A*对应着总成本C最小,其中如果实施成本增加更多,则可以选择吻合程度或者强制程度更小的问责,如果机会主义成本增加更多,则可以选择吻合程度或者强制程度更大的问责,以趋向节约成本的问责。
图2非营利组织的问责成本权衡
六、结论与启示
NPO问责对于监管组织、践行非营利使命、实现公共利益等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参考已有的问责分类,借鉴、运用威廉姆森的治理学说、布坎南和塔洛克的立宪学说,本文为NPO问责提供了一种新的分类标准——问责方偏好与NPO使命的吻合程度、问责方对负责方的强制程度,和新的分类——社会问责、自我问责、法令问责、层级问责。NPO问责成本可以分为狭义实施成本和机会主义成本,它们依吻合程度或者强制程度呈相反方向变化。原则上,各种类型的问责各有优劣,或者有实施成本的优势、但在机会主义成本上处于劣势,或者相反,所以问责类型的选择和设计主要是一个两类成本的权衡问题,而不同情境的最优问责有匹配的吻合程度和强制程度。
相比已有的成果积累,本文的贡献是为NPO问责提供了一个适于进行成本分析、权衡的分类框架,所以期望能够为实务操作提供一些指示或者参考性意见。例如小组织问责,由于资源、能力等局限,法令问责、层级问责的实施成本非其所能承担,所以应侧重于自我问责和小网络问责;还有服务过程、结果易于观察的组织,可以多利用组织外问责,以在实施成本较小的允许下充分抑制各种机会主义行为,而服务过程、结果不易观察的组织,则组织外问责的实施成本会不小,且易于引发逆向选择等机会主义行为,所以应相对重视自我问责和协作型问责;再有不同组织的问责,像会员型组织,应重视外部型问责,重点防范团体可能给社会造成的外部性,还有主要服务于弱势群体的服务型组织,由于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内外支持力量都薄弱,所以像司法、监管、协会等外部问责应重点保护他们,等等。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23][26]康晓光,陈南方.NGO问责——5.12大地震引发的一场“信任大地震”[A].卢宪英,韩恒.非营利组织前沿问题研究[C].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121-124,142-143,143.
Kang Xiaoguang and Chen Nanfang. NGO Accountability: Trust Earthquake Derived from 5.12 Big Earthquake. In Lu Xianying, Han Heng eds. Studies on Forefront Issues Concern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Zhengzhou: Zhengzhou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21-124, pp142-143, p143.
[2][3]李勇.非政府组织问责研究[J].中国非营利评论,2010(5).63,64-69.
Li Yong. A Study of NGO Accountability. China Nonprofit Review, 2010, 5. p63, pp64-69.
[4]康晓光,冯利.中国NGOs治理:成就与困境[A].[荷]丽莎·乔丹,彼得·范·图埃尔.非政府组织问责:政治、原则与创新[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29-144.
Kang Xiaoguang and Feng Li. China’s NGO Governance: Success and Dilemma. In Lisa Jordon and Peter Van Tui eds. NGO Accountability: Politics, Principles and Innovatio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29-144.
[5]K. P. Kearns.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Accountability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4, 54(2).
[6][24]B. S. Romzek and P. W. Ingraham. Cross Pressures of Accountability: Initiative, Command, and Failure in the Ron Brown Plane Cras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0, 60(3).
[7]于常有.非营利组织问责: 概念、体系及其限度[J].中国行政管理,2011(4).
Yu Changyou. Accountability of NPOs: Concept, System and Limits.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1(4).
[8]J. GS. Koppell. Pathologies of Accountability: ICANN and the Challenge of “Multiple Accountabilities Disorder.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5, 65(1).
[9]A. Ebrahim. The Many Faces of Nonprofit Accountabilit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No.10-069, 2010.
[10]B. S. Romzek. Dynamics of Public Sector Accountability in an Era of Refor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on Sciences, 2000, 66(1).
[11]P. J. May. Regulatory Regimes and Accountability. Regulation & Governance, 2007, 1.
[12][美]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的性质[A].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C].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4-57.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In R. H.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pp34-57.
[13][14][15][18]O.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pp47-49, pp45-46, 52-61, p21, pp148-153.
[16][17][21]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0-63,63-64,59-67.
E. G. Furubotn and R. Richter.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pp60-63, pp63-64, pp59-67.
[19]O. E.Williamson.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06-109.
[20][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5-48.
J. M. Buchanan and G.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 pp45-48.
[22]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87.
P. F. Drucker. 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p87.
[25][27]娜拉.中国草根NGO的问责现状与问题[A].卢宪英,韩恒.非营利组织前沿问题研究[C].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182-185,191-192.
Na La.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ccountability. In Lu Xianying, Han Heng eds. Studies on Forefront Issues Concern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Zhengzhou: Zhengzhou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82-185, pp191-192.
(作者: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南京210093)
A Cost-oriented Typology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ccountability
Chen Zhiguang
[Abstract]Based on coincidental degree of accountee’s preference and organization’s mission and coercionary degree of accountee over accountor,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typology for nonprofit accountability: self accountability, hierarchical accountability, social accountability, and mandate accountability. Accountability cost can be divided into enforcement cost in a narrow sense which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incidence degree as well as coercion degree and opportunity cost which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m. Accountability types’ selection as well as combination is a cost trade-off problem which means that optimal accountability in some situation has its own matching coincidence degree and coercion degree.
[Key words]Nonprofit Organizatio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ccountability; Enforcement Cost; Opportunity Cost
[Author]Chen Zhigu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