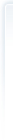
[编者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今年的相继离去,是包括中国行政管理学和政治学人在内的全球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本刊特以此译文纪念他们对于人类学术知识的卓越贡献。限于篇幅,原文的参考文献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原文。
*本文原载于美国《政治科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s of Political Science)2012年第13卷。译文获得该刊授权(版权号: 2970230190436 )。
作者致谢——在这个长途旅程中,我幸运地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包括福特基金会,FAO,麦克阿瑟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感谢Bryan Bruns, Michael Cook, Christine Ingelbritsen, Marco Janssen, Margaret Levi, Mike McGinnis, Roger Parks, 和YahuaWang,他们对于本文的初稿进行了富有见地的评价,Patty Lezotte对于本文进行了富有见地和杰出的编辑工作。感谢《政治科学年度评论》编辑委员会邀请我反思我的学术旅程。对于我来说,这是巨大的荣誉。
[摘要]本文讨论了我的个人经历、我们之中与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相关的许多人的努力,即研究在不同背景下,制度是如何影响行动和后果的。首先,我回顾了我作为年轻学子的经历和我的早期职业生涯,旨在激励那些面对难题的人们。然后,我讨论了我们的制度分析和我们对于都市治理和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这些研究帮助我逐步发展了分析复杂制度的较为一般的框架。这一框架已经能够使我们发掘和分析制度结构、行为和后果,做出和检验内在一致的预测,并且建立更好的理论。最后,我就未来学术发展方向,与大家分享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制度分析;集体行动;公共物品;公共池塘资源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12)09-0104-10
一、导论
在外人看来,也许当前我的职业是相当成功的,它一直如此吗?老实说,回答是否定的。我本科学习政治学基本是偶然的。幸运的是,在开始研究生学习之前,我有一段短暂的职业经历,否则,在我申请博士研究生学习时所得到的咨询意见也许会使我感到气馁。我的研究兴趣带我走过了跨学科的、研究复杂社会—生态系统的漫长道路——这条道路受到许多政治学同行的强烈批评。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制度最初如何形成,在许多不同的场域(settings)中它们又如何影响了人们互动的动机和结果。虽然我参与发展的理论是一般性的,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我进行经验性研究的大多数场域与我本人所从事的政治科学毫不相干。为什么要研究地方治理和政策、尼泊尔的灌溉问题、农民或者森林?人们期望一位政治学家研究国家或者国际体制中的国会、官僚,而不是低层次的规则制度的设计、运行和适应性。
20世纪80年代,我还参与了其他的实验性研究项目。当时,实验室的实验并不被政治学家看作是可以接受的研究方法。因此,随着我在制度研究方面的深入,以及对于其复杂性的认识,有些研究传统理论的同行们认为我分析多种多样的规则很“傻”。他们认为,这种复杂性程度是多余的,并且使得制度结构和结果分析变得十分困难。
因此,作为一名使用多种实证和理论方法、在多样和嵌套层次上提出与多重制度相关的问题的学者,我走过的路当然不会是一条直线,但是,我希望我能够描述我学术历程的一些片段,并且汇报一下我对于未来的看法。
二、我的个人经历和早期职业生涯
1.高中
同事们问我,是什么使得我成为一个政治科学家。一个答案是,我之所以成为政治科学家,是因为在高中时说话口吃。在我高中二年级时,有位老师很关心我的口吃问题,告诉我去参加演讲社团。我被指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背诵诗,但在第一次竞赛性演讲活动中,演讲队的其他成员都取笑我的“娘娘腔”。他们认为,所谓“真正的”演讲团队应该是辩论性的。所以,我就参加了竞赛性辩论并且感到这似乎很有意思,由此加入了争论性辩论队。在两年的辩论队比赛中,我与加州的许多其他 高中辩论队竞赛。学习如何辩论是学者生涯的一项重要经历。作为一个辩论者,你了解到,任何问题至少都有两面性,因为一场比赛的每个不同回合,你都很可能被指派到辩论的任何一方,而无论你被指派为哪一方,你都必须准备有效的论点和论据。
2.大学
当我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我是否可以将辩论作为专业。他们告诉我不行。我不知道毕业后想做什么,新生指导教师说,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最好的专业就是教育,以便毕业后当教师。所以,我就把教育作为我的初选专业。在第一学期,我选了政治学101号课程,一位杰出助教的课程令人振奋。我立即改选政治学作为专业。我还选了许多经济学和商学的课程。幸运的是,我的经济学学得非常好,在三年级时老师问我,是否愿意帮助批改新生的经济学试卷,这项工作我做了一年半。
这份工作是支付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费用的方式之一。我是家中的长女,我的父母都只是中学毕业,并且我母亲认为,大学是“无用的投资”,因为她在高中毕业后没有得到家中的支持而不得不去工作。因此,我本科期间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在夏天,我教游泳;在学期中,我在大学图书馆、当地一元店(dime)打工,还做过其它形形色色的工作,每周工作25-30小时。
1954年初,我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冒险去了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帮助我第一位丈夫进入哈佛法学院。
3.第一份全职工作
在1950年代,作为一名女性和新毕业的大学生,寻找工作是“富有教育意义的”(Instructive)经历。每天面试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否会打字和速记。在坎布里奇一家电子企业作为出口物资职员工作了一年后,我最终在波士顿一家从未雇佣女性担任秘书以上职位的杰出企业中获得了人事助理的职位。我自愿工作了几个月,未领取报酬,以使他们相信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这看起来是不必要的,但是我必须要不断地证明自己。1957年,我回到洛杉矶,申请洛杉矶分校人事办公室的一份专职工作,当我得知自己受到了波士顿雇主的强烈推荐时,我深感宽慰。这特别令人高兴,因为我打破了该公司清一色男性员工的局面。以前,所有的员工都是男性白人、清教徒或者天主教徒,包括几名新雇佣的男性黑人或者犹太人。
4.研究生院
当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作时,我认为自己需要获得公共行政的硕士学位。我选了每年开设一个学期的研讨课,确定我喜欢研究生学习,并且开始考虑获得博士学位。
在职进行硕士学习是寻常之事,但是,攻读博士学位并且获得奖学金以便能够进行全日制研究生学习,就完全不同了。我的经济学导师强烈建议我放弃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因为我的数学基础较差(由于之前缺乏学习指导)。但是,他却同意,如果我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可以辅修经济学。我的政治学导师则坚决反对我攻读博士学位,因为我已经有非常好的“职业”位置。他说,如果我拥有博士学位,最好的工作就是在某些城市学院教书,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我早先在坎布里奇求职的经历使我忽视了这些警告,并且申请了助理奖学金(assistantship),以便能攻读全日制博士学位。幸运的是,我获得了这个奖学金。
令人奇怪的是,那年,财政资助委员把4个资助奖励给了女生,而在此前的40年中,没有一名女教师或者女博士获得这样的奖励。我们4个人在学期中得知,这个决定在教授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有些教师认为,把40个奖学金中的4个名额授予女生,是对系里资源的浪费。他们担心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会取得良好的学术地位,这就会损害系的名誉。幸运的是,我们的研究生同学鼓励我们4人不要理会这些教师的担心,他们也建议我们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尽可能躲避这些教师。
政治学科过去分为政府研究与政治哲学研究(今后还会依然如此)。直到读到Mayr (1982)的《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一书,我才发现了一个观察核心概念的真正令人激动的“思想历史”,发现它们是如何被定义的,如何被构建成为一个理论,如何受到证据或者其他理论的挑战,并且与时俱进地发展的。在政治哲学课程中,人们经常被教之以生命、爱和各种各样的伟大思想家的思想,而不是理解一个学科发展深层次的核心理论。人们单个地研究霍布斯、卢梭、马基雅维利和洛克,但是并不努力探讨他们之间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在政治哲学课程中,托克维尔的开拓性研究和《联邦党人文集》很少被讲授,因为它们被许多政治学者认为只是对于特殊时期的描述性叙事,或者是新闻工作者为使公众支持一部新宪法而做的努力(见 Dahl 1956;V. Ostrom 1991, 1997)。
政府研究则按照地区或者区域划分,人们研究美国政府、比较政府,或者国际关系。在比较政府研究中,人们关注的是同一个洲。在标示学科专业(discipline)时,地理区域因而比理论重要。这种地理分界仍然是划分系和专业考试的主要方式,在某些系,两个领域——方法论和政策分析除外。如果一个人研究国际关系,他就要关注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许多政治学家的主导性观点是,政治科学是研究“国家”的,即使在如何定义这个核心概念上还存在许多分歧。比如,提图斯(Titus)(1931)就指出,国家的定义不少于145个。四十年以后,埃克斯坦(Eckstein) 评论道,“当代政治科学的许多独特方面之一”,就是“政治学家相当多地努力试图严格定义他们所研究的事物的本质。”(1973,P.1142)
那些研究比较政府的人努力理解如何比较大多数欧洲国家、某些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也许少数非洲国家的上院和下院的结构。对于大多数美国政治学家来说,非洲仍然是黑暗的大陆——至少在美国和平部队带回了大量未来的政治学家,从而使得非洲研究计划在几所主要大学中得以开展之前是如此。政党的角色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我的博士资格考试的问题之一就是,“比较英国、法国和(你自己选择的)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中两个主要政党的近期历史和作用”。另外一个问题是,“比较加拿大、德国和日本的上议院”。政治科学的研究生被要求比较、列表和描述,而不是考察与理论A或者理论B联系在一起的经验证据。
5.学位论文
特别幸运的是,我的第一份助理奖学金是在政府研究局。这就使我能够参与教师和高年级研究生会议,他们正在开始进行某些尝试,以政治经济学方法进行都市政府的研究。文森特等(V. Ostrom et al., 1961)写了篇开拓性的文章,即“都市地区的政府组织:一项理论探讨”,这篇文章被公开严格讨论了若干次。在我博士项目初期,我参加了文森特的地方公共经济组织研讨班。我永远感谢他,不仅因为他的知识洞见和多年的鼓励,而且因为他开启了Lou Weschler, Ellis Perlman 以及我们当中的其他几位令人激动的发现之旅。(这是我与文森特一起参加的最后一个研讨班,因为我们开始约会,并且最后结婚了)。他要求每个学生关心南加州的地下水域。我们的任务是考察每个水域处理(或者不能处理)越来越严重的污染和地下水位下降问题的过程,而政治管辖权与水域并不具有同样的边界(V. Ostrom1962)。
我被派到西部水域,这个水域处于洛杉矶和其他11个城市的地下。在20世纪前半叶,水的生产者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洛杉矶地下水位正在下降,海水正沿着海岸侵入。二次大战快结束时,若干城市的水部门要求美国地理调查(局)对这些地区进行调查,并且同意资助三分之一的研究经费。该研究报告详细描述了海水侵入的恐怖图景,这种侵入可能最终摧毁人类使用的该流域。
我出席了西部流域水协会(West Basin Water Association)的例行会议,这是一个私人性的、向该流域所有的水生产者开放的协会。结果,我为研讨班论文进行的研究逐步发展成为学位论文的研究。令人高兴的是,会上我可以根据“我的研究立场”进行半小时的发言。这种切近性,给予我许多机会,与许多地方参与者,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官员进行深度讨论;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查阅协会的档案,这些档案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用的;随后我还研究了不同地区试图解决这些复杂的政治问题的提案。
在研究单个案例的同时,我也参与了一个师生研究团队,研究了采用其他策略导致不同结果的若干案例。因此,作为一名研究生,我开始理解影响地方层次集体行动问题的其他核心因素。根据多年的研究,我现在认识到,西部流域问题的核心特点如下:
(1)巨大的数量。 涉及到500位水生产者,在规模上包括了从使用水井的个体农场主,到服务于大规模人口的市政水设施。
(2)法律的不确定性。(三种)相互矛盾的法律规则都可能作为分配水给不同的使用者的“特定”规则。
(3)不对称的利益。水井靠近太平洋的生产者透支最大,对于地下水的依赖程度,不同的生产者各不相同,而一项法律条文就可能导致具有实质性差别的赢者和输者。
(4)在“问题”与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匹配性。所有的相关部门都大于或者小于地下水流域,没有任何部门有权威贯彻实施一个方案。
这些特性存在于与一般的社会困境有关的情景中,尤其存在于与公共池塘资源相联系的情景中(Baland & Platteau 2000, Berkes 1989)。因为我已经研究了具有这些特点的案例,并且看到了创新性解决方案的发展过程,因此,当后来的理论强调,这些特点使得解决这样的集体行动问题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时,我是持怀疑态度的(Dawes et al. 1986, Hardin 1971, Olson 1965)。
在我进行论文答辩时,西部流域的地方行动者已经设计了一项复杂的多中心制度,它具有几个积极的方面。首先, 80%的水生产者达成法律协议,削减地下水的生产,这一协议由加州高级法院强制实施,每年向所有生产者进行年度报告,内容涉及在必要情况下调整水资源分配的服务情况和能力(Blomquist & Ostrom 2008);第二,水工程师开发了一个新系统,这个系统通过向沿岸及其周边地下陆地注入淡水的方式补充地下水。第三,生产者设计了一种新型的特别区,以便于他们要求自己的地方议员通过加州立法院引介这一新的系统。
这个制度真正是多中心而不是单一中心, 而单一中心是政治学科当时的支配性思维方式。一个国家机构——美国地理调查局——对于地方的要求和部分资助计划做出了反应。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洛杉矶县洪水控制区(the Los Angeles County Flood Control District)和都市水区域(the Metropolitan Water District)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没有核心权威。11个市政府也参加了——其中之一在早先有关水权的讨价还价中曾经寸步不让。几个大的私人企业,包括标准石油(Standard Oil)也参加了进来,该企业积极敦促其他生产者同意削减,以便使得所有人可以继续使用这个流域。
西部流域水协会的常规性会议使得多种多样的行动者结合到一起,在公开的论坛上讨论问题。这个制度并非是完美的办法,但是,比起这个地区其他流域和邻近州的其他办法来,它确实较好地解决了许多问题(Blomquist & Ostrom 1985, Weschler 1968)。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布卢奎斯特(Blomquist,1992) 曾在1980年代重新研究了西部流域和加州其他7个流域的绩效,结果表明西部流域的制度一直在有效运转。对于这个复杂的治理体系的持续研究表明,它是比较坚实(robust)的一套制度设计(Steed &Blomquist 2006),尽管由于与上游邻居之间存在某些冲突,以及某个公职人员把公共基金用于个人所有而存在着挑战。
承担这一项研究,使我对于建立在严谨的田野研究工作基础上的单个案例研究充满了深深的尊重。 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就可以全方位地了解同样的一件事,可以查阅书面通信和其他文件,分析历史资料,提出与相互冲突的信息相关的疑难问题,并且获得对于复杂过程的深刻理解。如同我的同事和我在后来出版的作品中阐述的那样(Poteete et al. 2010),单个案例研究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其中包含进行较大数量的田野研究、元分析、正式模型和实验性研究。人们不应该把其中任何一项看作唯一或者最好的研究方式。
1960年代我在西部流域进行研究时,无论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还是哈丁的《公用地悲剧》都尚未出版和发表。我把我的案例看作是影响一个地区的纠结性冲突的例子,这个地区不存在单一的政府,这一纠结性冲突之所以能够得到解决,是因为那些相关者的公共企业家精神,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其中开发出适用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解决方案。我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布坎南和图洛克的《同意的计算》(Buchanan & Tullock 1962)和斯蒂格勒(Stigler 1962)对于地方政府功能的研究及其对于熊彼特(Schumpeter 1942)的研究。
1968年以来,许多人关注奥尔森和哈丁的研究。哈丁正确地指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从公共池塘资源(如同他所描述的草场或者我们研究的地下水流域)攫取收益的每个人都力图尽可能多地攫取利益,以便成为短期的赢家,但是,这导致了所有人的损失。这种冲突也发生在西部流域。但是,在这个案例(以及我现在知道的许多其他案例)中,生产者并没有像哈丁描述的那样陷入困境。他们有州法院的法律条文,加州的水资源部,还有美国地理调查局,它们不仅能够给他们提供准确的信息,还能够给他们提供共同战斗以找到解决方法的空间。这实际上的确是一场战斗,如同与公共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许多集体行动问题那样(Dietz et al. 2003)。但是,我早就知道的是,面对这样的问题的个人,并不需要外部权威使他们脱离其悲剧。他们拥有这样的战场,在其中,他们可以与其他人协同,可以学会相互信任,可以获取可靠的数据,可以确保监督其决策,可以创立新的机构,可以不断适应,他们虽然并非总是,但是经常可以使自己摆脱这些挑战性的困境。
6.成为助教
当文森特受聘于印第安纳大学时,我没有受邀访问布鲁明顿(Bloomington),但是,幸运的是,印第安纳大学没有那种当时许多大学(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具有的裙带关系禁令,这种禁令可能排除我在校园的任何地方受雇的可能性。那个职位看起来对于他来说是相当好,我热切地建议他接受。
布鲁明顿的确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当我们1965年1月第一次到达时,我们幸运地发现环绕着大学的森林中有一大块土地。我们花费了第一个学期设计住房,并且在那个夏天与一群人一起干活,建造这所房子。文森特那时是《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的编辑,需要人帮助处理投稿论文和评阅意见。印第安那大学并不提供秘书或者研究助理来做这些工作,所以,我就非常忙碌地协助他。
1965年夏天,政治系的同事问我,是否可以给新生教《美国政府导论》,时间是秋季学期的每个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上午7:30。由于我做过的一项田野考察就是在美国政府中进行的,所以,承担这项访问助理教授(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的工作是相对轻松的。这门课我教了一年。在该系研究生课程指导教师成为系主任后,研究生指导委员会主席邀请我做研究生课程指导教师。他知道,我年纪不轻,并且具有相当的人事经历,认为我可以胜任它。我为这一工作感到高兴,但是,我建议他们不要想使一名访问助理教授成为研究生课程指导教师。这时,他们任命我为一名正式的助理教授。因此,在越南战争期间,我获得正式聘任,担任研究生课程指导教师一年,当时,每年秋季入学的班有近90名学生。毋庸讳言,在作助理教授的初期,我并不能开始我的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
我早期的职业生涯,与60和70年代的一般女社会科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同。能被研究生院录取是非常幸运的,找到一份助理教授的职位是不容易的,即使你的博士论文获得学术奖励。一些积极的行动政策(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创造了新的机会,改变了学术环境。一旦男同事发现能够与女同事进行非常惬意的学术互动,并且见证了她们的研究和教学能力时,女性的机会就多了起来。看到今天这一学术界的重要变化,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欣慰。虽然歧视并未消失,但是,录取女性进入研究生项目,成为助理教授,然后授予终身教职,已是大势所趋。过去的一些积极政策现在不再被经常提及,因为许多学校已公开聘任女性和少数族裔,并且作为平等的申请者加以对待。
三、我的研究
1.第一项治安研究
在我把研究生课程指导教师职位交给一位同事后,就有时间在1969-1970年提供为期一年的研究生研讨班课程,内容涉及与都市政府和公共物品及服务评估相关的理论。这个研讨班上的博士研究生包括威廉·鲍格(William Baugh)、理查德·顾瑞斯(Richard Guarasci)、罗杰·帕克斯(Roger Parks)、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和戈登·惠特克(Gordon Whitaker)。秋季学期使我们有机会阅读大量有关都市治理和服务供给的文献(Friesema 1966, Lineberry & Fowler 1967, V. Ostrom et al. 1961, Stigler 1962)。都市治理有两条主要的研究路径——都市改革与公共经济(V. Ostrom & E. Ostrom 1965)。当我们开始揭示这些路径下隐含的理论时,我们发现,两种途径都假定都市地区的政府规模影响着政府治理的结果(output)、效率、受益者的成本分配、公民参与和公职人员的责任,但是,所假定的关系是不同的。
都市改革的倡导者制定强有力的政策方案,以消除他们所谓的都市服务的“碎片化”。提供服务的是地方政府的多个部门,这被认为是混乱的,因而是无效率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以检验他们的假设和预测(Bollens & Schmandt 1970,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1966)。当选民一再拒绝他们的方案时,他们的反应是批评公民对于他们的忽视(Hawley & Zimmer 1970, Zimmerman 1970)。
都市改革途径的倡导者认为,政府部门的规模对于任何类型的物品和服务都是积极因素。但公共经济途径的学者认为,政府部门的规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取决于公共物品或者公共服务的类型(E. Ostrom 1972)。在涉及面对面的服务供给中——比如教育、政策制定和社会福利,政府规模的消极影响会明显一些;而涉及规模经济,比如高速公路和基础设施的供给中,政府规模的积极影响会突出一些(Hirsch 1964,V. Ostrom & E. Ostrom 1971, Stigler 1962)。
减少都市地区政府部门的数量,被支持都市改革途径的学者认为对于所有因变量都有积极影响。政治经济学途径则认为,都市地区政府数量的减少对公民参与和公职人员责任具有消极影响,但对结果、效率、成本分配的影响则取决于所涉及的物品或者服务的类型。
我们正好有一个“案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途径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作为印第安那波里斯的市长,理查德·鲁嘉(Richard Lugar)在1969年对印第安那波里斯县(Indianapolis County)的政府结构进行了改革。这一改革被称为“统一政府”(Unigov.)改革,它提升了市长的权力,削弱了较小的乡镇政府。他提出,这是印第安那波里斯县所有地方政府进一步整合的第一步。但是,在我们的研讨班进行时,这个计划并没有向前推进。
罗杰·帕克斯(Roger Parks)对于如何研究印第安那波里斯的治安有一个奇妙想法。他指出,有三个独立的小警察局,这些警察局服务于与几个地区毗邻的社区,这些地区在社会经济方面非常相似,由更大的印第安那波里斯市警察局服务。这给予我们一个方便的研究机会。我们基于严格的方法论基础,通过调查研究,评估了6个都市毗邻地区的治安绩效(Wilson 1966,Wolfgang 1963)。幸运的是,在研究生课程以后,我教授一门春季学期的本科生荣誉研讨课,参考了大量有关地方公共经济和公共服务测量的文献。荣誉学生想要做些与常规班级不同的事情,所以,我建议他们与研究生研讨班一起,探讨一种严格的方法,来研究警察部门规模的影响。荣誉班非常热情而努力地与研究生共同工作,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发展了我们自己的调查工具,并且广泛地测试了它们。利用罗杰(Roger)关于印第安那波里斯的知识和人口普查图,我们可以描述6个毗邻地区的非常好的可能性样本。我没有外来的研究基金,但是,校园都市事务中心支持我们的研究,租赁印第安那大学的面包车送我们去印第安那波里斯市。
因此,我们的第一项研究工作就是检验关于都市治理的两种相反理论,关注于政府部门规模而不是部门数量。我们的研究引起了一些令人惊奇的发现——至少对于那些认为大都市政府总是生产优质的公共服务的学者来说是如此。与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警察局服务的地区相反,由他们自己较小的警察局提供服务的这三个地区的居民面临着较低的犯罪率;当他们遭遇犯罪时,更愿意给警察打电话;更能得到较高水平的服务跟进;对警察局绩效的评价更为积极。(见E. Ostrom & Whitaker 1973 and E. Ostrom et al. 1973,里面有我们研究结果更详细的介绍;以及Blomquist & Parks 1995a,b,里面有发现20年后相似模式的后续研究)。
在学期中,几位黑人学生问我,为什么我要研究白人社区的“共同体控制”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于都市地区的黑人来说更加重要。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什么地方黑人社区有他们自己的警察局,并且靠近大的、中心城市警察局。他们描述说,这样的地方位于芝加哥南边。我建议他们前往,并且与这个黑人城市的社区官员交谈,看看他们是否支持这项研究。如果回答“是”,那么,我将前往芝加哥警察局,看看我是否能够于秋天在印第安纳大学教授一门“非裔美国人”的本科生课程。所有调查的结果都是肯定的。
1970年夏季,我撰写了第一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项目书,目的是使用 “类似系统”的研究设计进行一系列未来的研究(Przeworski&Teune 1970)。按照这个设计,社区是相似的,但由不同规模的地方政府提供服务。我的计划是,采取多种研究方法,包括调查、分析市政内部记录、随机选取执勤警车并随访,这样可以观察到警民互动的第一手资料。虽然我是一个年轻、没有终身教职、而且没有一份丰富的论文发表记录的教员(见 E. Ostrom 1968, V. Ostrom & E. Ostrom 1965),但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我已经显示出设计和实施严谨的研究的能力,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尝试就获得资助的一个重要因素。后来我出版了一本书,因此在1974年获得了一个主动的聘任。
1970年秋天,我与几个杰出的黑人学生一起,对两个贫穷、独立的黑人社区进行了研究,并把这两个社区与由芝加哥警察局服务的三个类似社区进行了对比。当时,两个社区只有几名警察,他们的工资很低,警车经常坏,因为他们的预算非常有限。芝加哥警察局则有12500多名警力,他们的工资相对较高。我们估计,芝加哥警察服务的花费是那些小社区警察支出的14倍(E. Ostrom & Whitaker 1974)。但是,尽管在支出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我们仍然发现,一般情况下,在小城市生活的居民,与在芝加哥生活的居民相比,受到的服务并没有差别甚至水平更高。虽然犯罪率相同,但是,生活在独立的小社区的居民不太可能因为害怕犯罪而待在家里。在他们看来,当地的警察能够按照法律平等地对待所有公民,关注普通公民的需求,并不受贿。从这些初步研究中得到的发现与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致的(E. Ostrom & Whitaker 1974)。
深度的案例分析就其内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来说是强有力的。但是,研究发现也许只是反映了所研究对象自身的特点。为了验证其外部效度,我们根据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1966年针对万人以上的109个城市的2000余名公民所进行的大规模调查(E. Ostrom & Parks 1973),为城市年鉴增补了城市规模与支出水平方面的数据。我们发现,城市规模与支出水平之间存在一致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支出水平与公民对服务的满意度没有相关性。比如,害怕受到攻击或者家宅被人闯入,与城市规模具有正相关关系。
当时,我们在圣路易斯都市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这个地区由两个大警察局提供服务(拥有2200名警员的圣路易斯市警察局和拥有436名警员的圣路易斯县警察局)。在圣路易斯县,93个各自组成的社区有它们自己的警察所,其规模从10名到76名全职警察不等。我们研制了一个“最类似系统”的研究设计,研究了45个样本地区,这些地区跨三个毗邻的地段分布,这些地段在财富和年龄方面类似,并且分别由从小到大不同的警察局提供服务。我们发现,在毗邻和家庭受害比率方面,警察局规模与警察服务的人均成本之间存在明显而重要的正相关关系,而与认为警察反应迅速、工作杰出或者忠诚的受助家庭的比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E. Ostrom et al. 1973)。
我们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Grand Rapids)(IsHak 1972)和田纳西州那什维尔-戴维森县(Nashville–Davidson)(Rogers & McCurdy Lipsey 1974) 也进行了同样的调查。在整个研究中,没有发现单独的案例,即在提供毗邻地区服务的多项指标方面,集中的大警察局始终能够做得比小警察局好。
因此,我们为政治经济途径设定的相关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对于警察来说,政府部门的规模始终对于服务供给的结果和效率具有负面影响。为什么?
我们努力想弄清楚,为什么较小的警察局始终做得比训练更好、资金更多的毗邻大警察局要好。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研发了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概念(Parks et al.1981)。这涉及到消费者/公民与其官方生产者的努力。对于政府来说,生产高速公路和其它物质性基础设施,没有公民积极参与是可行的。但是,我们观察到,在我们研究的中小型社区中,公民与他们的官员能够更加有效率地一起工作,而且这种合作对于警务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较小的社区,公民积极监督他们的邻居,当令人怀疑的活动或者犯罪行为发生时,能迅速报警。而对执勤警察的随访观察显示,小警察局的警察更加了解他们的服务地区。因此,在都市地区的正式服务生产中,不仅存在政治经济学途径指出的那种规模不经济,而且人类服务仅仅由官方提供也不可能有效率。公民是重要的合作生产者。如果他们被看作无关紧要和毫不相干,那么,他们自然也不会积极合作。
2.研究复杂都市系统
我们对于都市治理的最初研究集中于生产服务的政府规模的影响上:政府部门的规模如何影响服务供给的产出和效率。在结束了一系列累积性的研究后,我们转向更难的问题:大都市区政府数量对服务供给有何影响。当国家科学基金国家需求应用研究部(Research Applied to National Need (RANN) Division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请求我们研究都市区服务供给的组织体制时,我们非常高兴。当然,当我们得到资助时,我们更加高兴!
先前的大多数研究认为许多大都市政府在同一地区运用多个部门提供服务时加剧了混乱。很少有人试图用经验研究来弄清楚官员与公民创立的组织结构以及该结构的影响。考虑到此前已有关于公共服务产业的理论成果(Bish 1971, Bish & Ostrom 1973, V. Ostrom et al. 1961),我们打算以连贯统一的方式测量组织间结构,而不是像学者们传统上所做的那样,认为简单地列一个清单就行,并且认为这个清单就是改革所必需的。
根据多年来我们与警察和警长的交流讨论以及新的研究计划,我们把大多数都市区提供的丰富多彩的公共服务分为两类:直接服务和中介服务。直接服务包括巡逻、对交通事故或犯罪行为的迅速反应和调查。尽管警察部门是当地居民所需的直接服务的提供者,他们也是一系列中介服务,如拘留、基本训练、犯罪实验设备和调度的消费者。中介服务的生产者可能是警察部门,也可能不是警察部门。
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研发出严格的方法,用以分配工业市场中特定的私人物品与服务的购买者和消费者,但是很少有学者致力于如何对这一结构进行测量,也很少有人研究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的后果。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方法,用服务结构矩阵描述组织间结构,并在80个都市地区对它进行测量,然后系统评估组织结构如何影响服务绩效。
虽然我们研究的都市地区有许多警察局为之提供服务,但是,却很少有重复的服务提供给同样类型的公民(E. Ostrom et al.,1978a)。此外,先前对在同一都市区不同部门提供同一服务会产生负面作用的假设并不成立。事实上,“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相对于生产者较少的都市区,高度多样性的都市地区中最有效率的生产者产出更多” (E. Ostrom & Parks 1999, p. 287)。改革者们认为,规模较小的部门不是犯罪的温床,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警察部门早就知道这些!大多数都市地区仅有一个犯罪实验场所提供服务,它们通常在医院里或较大的警察局里。我们研发了几项测量技术效率的方法,结果发现,在那些自动巡逻更多的都市地区,其技术效率水平更高(E. Ostrom & Parks 1999, p. 290)。然而,在由较少生产者提供犯罪实验室服务和无线电通信(两者都是间接服务)的都市地区,其技术效率也提高了。
通过系统研究警察的现场服务和仔细收集80个都市区的相关数据,我们否定了指导现有都市改革的理论。在《都市治安模式》(E. Ostrom et al. 1978a)一书中,我们指出,在涉及到都市治理时,复杂性不等于混乱性(see also McGinnis 1999,E. Ostrom et al. 1978b)。当我们对世界资源系统的治理进行经验研究时,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3.研发制度框架
除了进行研究以检验都市改革和政治经济学方法,进而理解上世纪70年代的都市治理外,我还组织了一个“制度安排的微观分析”的研究生班。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也主持了类似的研讨课,讨论在国家或者国际层面上民主行为及其后果对制度设计的影响。我们的研讨班是在政治科学系举办的,但是,我们的同事并不喜欢我们的方法,因为我们既采用经济学理论又运用了政治思想。经常有人建议研究生们不要选我们的课。幸运的是,注册人数虽然少,但是还是足以允许我们发展制度分析的方法。
1980年秋季,文森特参加了比勒费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比勒费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Bielefeld University)主持的一项长达一年的研究计划——“公共部门的引导、控制和绩效评估” (see Kaufmann et al. 1986)。我用我的第一个公休假,于1981年春天和夏天参加了这一研究小组,1982年夏季回到印第安纳。在我们两个人的知识之旅中,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与来自多学科的学者——包括克里斯托弗·胡德(Christopher Hood)、弗朗兹-克萨维尔·考夫曼(Franz-Xaver Kaufmann)、汉斯昆特·克鲁塞伯格(Hans-G¨unter Kr¨usselberg)、贾恩多梅尼戈·马琼(Giandomenico Majone)、保罗·萨巴蒂尔(Paul Sabatier)、赖因哈德·泽尔滕(Reinhard Selten)、马丁·舒比克(Martin Shubik)等在一起进行学术研讨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发展有关制度分析的观点,而不必拘泥于单一的学科。如果没有建立跨社会科学的共同语言,我们不可能发展出跨学科的方法,以用于公共部门中的引导、控制和绩效评估!我幸运地得到赖因哈德·泽尔滕的邀请,他让我参加他在比勒菲尔德大学举办的博弈论研讨班。在校园后面森林的漫步中,赖因哈德与我讨论了制度分析的演进框架和博弈论对该框架发展的核心价值。
拉里·凯瑟(Larry Kiser)和我撰写了一篇名为 《行动的三个世界:制度途径的元理论综合分析》的论文(Kiser&Ostrom 1982)。在比勒菲尔德,我进一步发展了制度分析方法,这为我未来几十年的大多数工作奠定了基础(E. Ostrom 1986b)。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如何为制度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并开发一个统一的框架,以分析复杂的政治经济活动中的立法机关、公共部门、市场,以及许多其它结构体,是我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在上个世纪探讨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中(Dahl&Lindblom1953),“制度”并没有出现在索引或者目录中。当时,作者讨论的是“规则”,他们讨论各种各样的规制形式和官僚的繁文缛礼。
博弈论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它使我们能够研发出描绘特定情境的数学模型,并预测理性个体在此情境下的预期行为。为了阐明博弈的结构和预期结果,理论家必须假设(a)行动者的数量;(b)行动者的位置,如先行者,或前排队员;(c)决策树中参与者在特定节点的行动集;(d)在一个决策点上适用的信息量;(e)行动者相互影响的后果;(f)描绘决策点上行动者和行动的间接或最终结果的函数集;(g)行动和结果的收益和成本。
我认为,一次博弈的作用过程(the working parts)实际上可被概念化为一种普遍的作用过程,即拉里·凯瑟和我所谓的“行动情境”。早先的学者运用交易 (Commons 1924)、框架(Goffman 1974)、情景逻辑(Popper 1961)、集体结构(Allport 1962)及脚本(Schank & Abelson 1977; 更为当前的观点参见 Levi 1990)描述这一过程。当我和我的同事研究警察时,我们发现有多种多样的行动情景——包括官员和公民在大街上或犯罪受害者的家里的互动,官员和官员在警车中的互动,调度员与官员的沟通,市政委员会会议,等等。我认为,我们可以用一系列共同的结构性要素分析政治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许多情景,然后解释为什么某些特定的行为和结果会在此类结构中发生,而不在其它结构中发生。
虽然理解一次博弈的作用过程为我们构建统一的方法进而分析行动情景的多样性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这些基础几乎无助于理解为什么各类文献都认可的行动情景(如官僚制、选举,或者立法机构)拥有不同的结构。经济学家提炼了影响市场行动情景的一系列比较清楚的因素,但是即便如此,为什么一个市场仅仅有一个垄断者,而另外的市场却具有许多生产者,这一问题仍然没搞清楚。大多数分析家从对当前结构的详细阐述开始,然后检验在市场体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所发生的变化,而没有分析从一开始就影响着市场结构的规则和其他影响因素。政治学家都知道选举法对两党制组织或者多党制组织出现的可能性及政治家的策略有广泛的影响,但是,他们经常围绕什么是模式化所有选举行为(或立法行为,或官僚行为)的“最好”方式进行争论,好像只存在着唯一的一种结构!
因此,我认为,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是开发出共同的语言,以便考察不同的行动情景的深层结构。从我们早期的关于产品特性的研究来看,很显然,这个基础结构的一部分来自生物物理学界。从与地下水和警察服务相关的田野研究中,我了解到,基础结构部分来自于参与者的共同体背景。除了行动情景的生物物理学和共同体基础之外,我想更好地探求相关正式运行规则与行动导致结果的结果性行动情景之间的关系。这促使我开始思考七种不同类型的规则,这些规则可能影响一个行动情境的七个组成部分。后来,我把这些规则概述如下(E. Ostrom 1986a):
(1)位置规则,它说明了一系列位置,以及多个行动者是如何相互制约的;
(2)边界规则,它说明行动者如何被选择进入或者离开这些情境;
(3)权威规则,它说明在一个节点上如何保证某一行动在特定位置出现;
(4)聚合规则(比如多数同意规则或者全体一致规则),说明在一个节点上行动者的决策是如何转化为间接或最终结果;
(5)信息规则,说明行动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什么信息必须、可能或者决不能被分享;
(6)范围规则,说明可能受到影响的结果;
(7)收益规则,说明收益和成本如何被分配给特定位置上的行动者。
为了说明构成行动情景基础的规则的有效性,我以当选人和公共官员间围绕预算-产出组合如何服务于公民的谈判模式为基础进行了几项重要且广泛的研究。唐斯(Downs,1957)、尼斯坎南(Niskanen,1971)、罗默和罗森塔尔(Romer & Rosenthal,1978) 以及麦克奎尔等人(McGuire et al. 1979)都对一次谈判博弈中的均衡解作了不同的预测。当时,分歧在于谁的模型是正确的。我的分析表明,他们都是正确的,尽管每个模型的背后规则都存在差异性。
四个模型的不同点在于,是否假设边界规则允许一个以上的官僚与当选官员进行谈判,权威规则是否赋予官僚领导者或当选官员控制议程的权力,在没有取得共识时,聚合规则是否阐明了可能导致维持现状或消失的预算水平。唐斯预言,谈判的均衡结果是中间选民的最佳策略。尼斯坎南认为,均衡将会是最大的预算-产出组合,以便能够在孤注一掷的投票中赢得大多数选票;罗默和罗森塔尔认为,在均衡解中,中间选民认为维持现状的比例几乎一样多;麦克奎尔等人则指出,允许不同的官僚机构参与谈判过程会产生一个均衡解,使得选民获得最大的净值。我们自己对于都市地区警察服务成本函数的经验研究为多个官僚机构参与时投票者预测更佳的结果提供了经验支持。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在检验先前假设的竞争模型中的特定规则时发现了为什么对于“同样的”谈判情景学者们作出的预测如此大相径庭。但是,我的某些研究公共选择的同事却非常不安,因为他们认为我的七项规则的学说为研究制度安排增加了太多的复杂性。
定义七种影响博弈行为组成部分或行为情境的规则不是我致力于理解规则的最后努力。深受约翰 R·康芒斯(John R. Commons)作品的影响,我认为,不管人们把行为或事件定义为是必需的、禁止的还是允许的,规则的独特性都是存在的。然而,一旦你研究了更广泛的关于制度的文献,你就会发现,“规则”、“规范”和“策略”的定义都是混乱的、重叠的。苏·克劳福德(Sue Crawford)和我花费了好几年时间广泛阅读了这些文献,发现我们处在“学术通天塔”(Tower of Academic Babel)中见Crawford & Ostrom (1995)一书的表1和2对于学者使用术语进行了丰富的排列,说明了他们的定义如何相互交织。Levi (1988)讨论的问题是,规范约定是用于规范主体必须做、必须不做或者可能做的,统治者对于没有共同规范约定的主体实施规则,是何等困难。。然后,我们创造性地开发了一个累积性的序列,使得进行制度分析的未来工作具有共同的基础(Crawford & Ostrom 1995)。当我回到更加集中于研究突出的环境问题时,这些在更为一般性的理论理解上的努力非常有用。
4.回到公共事物
经验研究发现,地方使用者有能力解决公共事物问题,这与盖瑞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观点相反(Berkes 1985, 1986; McCay & Acheson 1987; Netting 1972)。直到现在,人们仍然普遍相信资源使用者不可能克服这样的难题。对于这一分歧的关注导致了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的成立,以研究不同的公共池塘资源(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6)。
后来,在我撰写学位论文,研究西部流域的水生产者如何解决他们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正在研究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我更没有意识到在大家看来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当我应邀参加国家研究委员会公共产权制度的项目时,我已经准备转而迎接这样的挑战,即弄清楚为什么有些使用者克服了他们面对的公地悲剧,而另一些使用者自我堕落,毁灭了宝贵的资源。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主要活动是把不同学科的学者聚合到一起,成为一个研究团队,讨论他们自己的经验研究。考虑到不同学科强调不同的变量,委员会请罗纳德·奥克森(Ronald Oakerson)提出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IAD),以便在研究计划会议上学者们使用相同的框架讨论他们的案例(Oakerson 1986)。
不久,尽人皆知的是,来自多个学科的学者们研究了至少1000个案例,这些案例来自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不同资源。为了从这些没有经过整理的案例中获得某些知识,威廉·布卢奎斯特(William Blomquist)、詹姆斯·温奇(James Wunsch)、埃德拉·施拉格(Edella Schlager)、S.Y.唐(S.Y. Tang)、莎伦·胡克费德特(Sharon Huckfeldt)和我逐步研发了一个使用IAD框架的公共池塘资源数据库。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关于使用者与渔场、森林、灌溉系统和其他面临挑战的资源的关系的、大规模的、可靠的数据库。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记录了其学科认为比较重要的变量信息,但是忽略了那些被认为无关的其他变量。我们花费了数年时间,用于筛选案例,评估所收集的数据的质量和适用范围,记录含有关键信息的案例,并在发现数据质量有待提高时,与案例作者核商并进行仔细的分析。最终,在灌溉(Tang 1991, 1992)、渔场(Schlager 1990)、正式模型关系的跨部门分析(Schlager et al. 1994)、进行试验以检验特定假设上,我们的集体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E. Ostrom et al. 1992,1994;E. Ostrom & Gardner 1993;Weissing & Ostrom 1991)。
运用CPR数据库进行的比较分析也支持我们关于产权概念的系统界定。许多学者认为,只有使用者有权利将其受益权销售(让渡)给他人时,产权才存在(Demsetz 1967)。按照这个观点,不能把他们的权利销售给其他人的使用者,实际上是没有产权的。与之相反,施拉格和奥斯特罗姆(Schlager & Ostrom,1992)发现,使用者进入、离开、管理、排他和让渡的权利都是重要的权利,普遍具有累积意义。比如,假如没有进入权,那就不可能实施离开权的。这就为我们分析可能的权利等级体系中的一系列权利束时提供了的新的概念术语。一位被授权的使用者只有进入权和离开权。一位原告拥有这些权利和管理权。业主权增加了排他权。所有权包含了全部的权利。CPR数据库中的案例证明了各种各样的权利束,并表明,为了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使用者不需要让渡权。如今,这一产权概念已经被全世界研究不同的产权制度的学者所接受(Brunckhorst 2000, Degnbol & McCay 2007, Paavola & Adger 2005, Trawick 2001)。
5.为写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而奋斗
当我有独特的机会安排上我的日程时,我们积极地对CRP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了编码和分析。诺斯(Doug North)听取了我所做的关于制度分析和公共产权典章的制度发展的演示讲解。他非常热情,敦促我为他和吉姆·阿尔特(Jim Alt)主编的丛书撰写一本,该丛书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后来,吉姆·阿尔特和肯·谢普瑟(Jim Alt and Ken Shepsle)请我把在哈佛大学进行的五次讲座编辑为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成为这本书的草稿。1986年秋这个邀请得到进一步扩展,在此之前我已经利用另外一个春假在德国的比勒菲尔德跨学科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ZiF))进行了研究。赖因哈德·泽尔滕组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小组,该小组由社会科学家和生物学家组成,考察生物和社会系统中如何运用博弈论来理解互动及其结果的模式。我到达以后,第一个研讨班的题目是“为什么具有性别?”显然,我出席了这个研讨班。我逐步惊奇地认识到,存在两种性别而不是一种性别,这是一种无效率的再生产方式。研讨班的问题是严肃的,并且被许多杰出的生物学家所研究。
在同一时间拥有一个假期和这些各种各样的邀请,使我认识到我应该写一部书,分析我们能从个案研究中得到哪些教训,以及我们对于特定问题的统计分析。我梦想在已经编码的元分析中分析某些规则,进而发现那些在一般意义上与长期成功相关的规则。我花了好几个星期重新阅读这些案例,对之进行重新撰写和统计分析,我觉得自己真是个笨蛋,因为我不能在那些关于产权的成功案例中发现某些规律。最后,我豁然开朗,我应该放弃寻找那些能够产生成功的特定规则的这一目标。也许我需要做的是转换到更一般的层次,发现业已存在很久的系统中某些更普遍的制度规则。我甚至不知道我该怎么称呼这些规律,但是,后来我灵光一现,讨论它们的方式其实就是“设计原则”。
我认为,那些发明并且成功地将公共产权制度维持了数个世纪的灌溉者、渔民、森林居民和其他人并没有在他们的大脑中形成明确的原则概念。在绘制一幅杰出的艺术作品时,并非所有艺术家都是经过艺术训练并且了解设计原则的。我认为,这些制度规律性就是潜在的设计原则,人们可以从长期持续的体制中抽象出来。接下来的任务是把它们与失败的案例进行比较,然后评估这些失败的案例中是否含有同样的原则。当然,如果有,这些原则无法提供一个对可持续系统和不成功系统的有意义的区分。但是,比较研究显示,失败案例的特点并不包含这些原则。
在比勒菲尔德奋斗并演讲的几个月后,我于1988年4月在哈佛大学进行了首次系列讲座。那里的同事们给了我积极的反馈。我记得与肯·谢普瑟(Ken Shepsle)、吉姆·阿尔特(Jim Alt)、鲍勃·普特南(Bob Putnam)进行了精彩的交流。幸运的是,道格拉斯和吉姆在讲稿提交之前给了我大量的时间修改初稿。在我自己的地下水制度发展之外,我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案例研究。我把所有章节发给原始案例的研究者,以便他们能够批评、甚至推翻。我不想把我的结论建立在对他人案例研究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
当把这本书寄给剑桥大学出版社时,我相当忐忑,因为我不确定这些设计原则到底会被看作一系列观点的疯狂集合,还是对潜在规律性的一种发现。
现在看来,这种努力是值得的。许多学者阅读了《公共事物治理之道》,并且发现,在他们的研究中,那些坚实的、自组织的系统都具有该书所描述的设计原则的特征,而失败的系统则没有这些特征。因此,1990年我列出的设计原则得到了绝大多数的实证支持。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的几位访问学者和研究生开发了一个数据库,来记录他们在文献系统搜索过程中的研究信息(见下文“创立促进知识合作生产的环境”)。他们区分了111个灌溉、近海渔场、牧场系统和森林的经验研究,记录了地方制度的设计信息。在一篇最近发表的论文中,考克斯等人(Cox et al..2009)发现,只有10%的研究无法证实有助于解释有效的设计原则的长期可持续性。许多学者提供了关于改进这些研究的细微方法等有益建议。考克斯和他的合作者已经开发出几个有用的复制模型,并提醒读者不要把“设计原则”与“设计蓝图”混淆。
6.对公共事物的进一步研究
除了我们早期进行的自组织研究以及管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公共产权制度的坚实性研究之外,研究所的相关同事还积极进行灌溉资源和森林资源的深入研究。我们运用此前开发的编码格式对公共池塘资源数据库进行元分析,以此作为研究全世界森林制度和森林本身相关的数据库的基础。我们并不想仅仅关注社区管理的资源。我们也研究政府拥有和管理的、私人拥有和管理的、共同管理的、社区管理的甚至无人管理的制度(开放进入)。
我们在十二个国家间建立了一个合作研究中心网络。每个中心都有它深入研究的主题。根据很久以前我们在第一次治安研究中的教训,我们确信:知识的合作生产是必要的。美国的学者跑到海外研究各种各样当地的情况,然后再回到美国,这样一个国际项目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人需要合作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每个人使用同样的潜在逻辑和数据登记表格来收集和登记数据。国际森林资源和制度(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s (IFRI))网络中的每个研究者生活在他所研究的国家,并对改进森林的可持续性和依赖它的人们有持久的兴趣。
早期研究得出的某些结论得到了再证实。我们发现,对于当地的森林使用者来说,自我组织起来以及开发其管理森林的一系列规则是可能的。有些团体努力过,但是失败了,而其他团体成功了。还有一些团体从一个系统开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系统崩溃了。关键性和强有力的发现在于,对于资源的使用者来说,自我管理并不是不可能的,哈丁早先坚信这一点,许多学者到现在仍然相信这些。
此外,我们发现一些国有的森林运行得很好,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规模维持在合适的水平上。一些私人的和共同管理的森林资源也是如此。换言之,不是森林治理的一般类型造成了这些差异性,而是下列因素造成了差异:特殊的治理安排如何适应当地的生态、特定的规则如何形成并随着时间发展而加以修正以及使用者是否认为制度是合法的和公平的。而且,多项研究都证明,影响可持续性机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使用者自己是否参与了森林中活动的日常监管(Coleman 2009, Coleman & Steed 2009, Gibson et al. 2005, Hayes 2006)。使用者监管的重要性使有些学者感到吃惊。但是,田野调查和实验研究使我们始终坚信,构建以他人普遍认同为基础的信任,对于维持长期进程中规则的一致性资源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7.创立有利于知识合作生产的环境
多年来除了研究该领域的合作生产之外,我们发现使教师和学生参与他们自己的合作生产活动特别重要。上述所说的合作研究中心就是一个例子。上世纪70年代初期,伴随着学术讨论会制度的建立,我们就开始认真地讨论制度理论,这些讨论会每周一中午定期举办。人类学、商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政治学以及偶尔来自其他学科的教师和研究生们聚在一起,围绕不同政治经济结构的多样性、激励机制和产出模式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到2009年6月,这种专题研讨会举办了902次。这些讨论开阔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强化了我们的研究设计,并且帮助我们成功地申请到资金。
由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命名的“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所于1973-1974学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创立。我们非常幸运地与几位工匠一起建设了我们的家园,添置了大多数设施,并在加拿大休伦(Huron)湖畔的马尼图林(Manitoulin)岛上建造了一个小木屋。我们学会了尊重研究所中的创造性的、严谨的工艺。研究中心的愿景是当研究生与来自不同学科、运用多种方法进行设计并进行精心研究的老师一起工作时,他们能够增强自己的技艺(见 Aligica & Boettke 2009, V. Ostrom 1980)。去年,研究所以自组织会议的形式庆祝了其35周年,会议吸引了来自27个国家的144名学者参与,主题是:“横跨全球的研究者们: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8.下一部著作
当我2009年夏天撰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对一部书稿进行最后的修订,这本书名为《共同工作:实践中的集体行动、公共事物和多元方法》,合作者是艾米·珀梯特和马克·詹森(Amy Poteete and Marco Janssen),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Poteete et al. 2010)。我们讨论了单个的案例研究、多案例的元分析、以田野为基础的大规模比较研究、正式理论、实验研究以及把理论与代理模型结合起来的新方法是如何有助于理解集体行动理论的,正如这些理论可运用到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中。把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聚合到一起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假如外界对于书稿的评论哪怕反映了未来关于该书反响的一丁点信息,它将会推动我们的理解向前发展。而且,我们非常希望打破即使在同一个学科中因运用不同研究方法而人为被隔开的壁垒,更不要说跨学科的界限了。
9.下一个项目
2007年,马蒂·安德瑞兹(Marty Anderies)、马克·詹森(Marco Janssen)和我组织了一个国家科学研究院学报(PNAS)的专辑:“超越万灵之方”(Going beyond Panaceas)(E. Ostrom et al.2007)。我发展了一种分析社会—生态系统中相互关系的框架,这一框架能够为一种诊断理论(Diagnostic theory)提供基础。2009年夏天,《科学》杂志发表了我的论文“一种分析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一般框架”。这使我能够获得跨越不同学科的广泛学者听众,来更新网络化的、多层次的框架,以便分析多元主体和内嵌于治理体系的资源运用体系如何影响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这样的理论问题。欧洲、美国多所大学的学者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同事与我共同工作,在一个名为 “分析社会生态可持续性的诊断性本体论”(Diagnostic Ontology for Analyzing Social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DOSES)的项目下开发这一框架 。DOSES将成为国际学者们使用的共同框架,用来分析供水系统、乡村系统、渔业和城市基础设施,以及通过IFRI网络持续进行的森林系统研究。DOSES发源于IAD,并把它作为核心组成部分,但是又明显包含了关键的生态层组的多样性举措(measures),用来弥补社会和制度举措的不足。
四、未来制度理论面临的知识挑战
虽然1960年以来制度学者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一个主要的挑战是继续剖析那些影响行动情景的因素。DOSES项目将这一问题放在社会—生态系统中解决,我希望其他学者能在其它政策领域中回应这一挑战。年轻的学者现在有大量的机会在其早期职业生涯中开发严密的数据库,这有助于他们能够长期研究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
第二个主要的挑战是个体选择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能够将其用于不同的制度场域中。当易犯错误的、不断学习的个体在不断重复的简单的情境中互动时,假如他们拥有与决策相关的变量的完整信息,那么,使之模型化是可能的。在高度竞争性的环境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如果个体是特定环境中与生存相关的关键性变量的最大化者,那么,这个人就会在环境的选择性压力中幸存下来(比如,获得收益或健康)(Alchian 1950)。当个体面对相对简单的决策情境,且制度含有相关问题的精确信息时,问题就是明确的、受最大化限制的问题。与IAD和DOSES框架是一致的、成熟精确的个体选择理论——博弈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包含极端的设定,如无限的计算能力和个人净收益的完全最大化。当在产权被清晰界定,且在买卖双方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基础上予以实施的情境中讨论私人产品市场时,以充分信息和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市场行为及其后果理论能够很好地预测产出。
但是,用于理解地方公共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的许多利益情境更加复杂,它们涉及更大的不确定性,并且缺乏充分竞争性市场中的选择性压力和信息生产能力。因此,我们需要用有限理性替代公理式的选择理论(信息是完全的和效用最大化的假设),转而认为个体虽是理性的,但理性有限度(见 E. Ostrom et al.1994, ch. 9; Simon 1965, 1972; Williamson 1985)。 信息搜索成本高昂,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个体必须经常以对所有可能方案的不完全知识和他们偏好的结果为基础做出抉择。在选择实现自身目标的策略时,所有的个体都可能犯错误(V. Ostrom 1986)。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其所处的情境,采取措施获得更高的回报。互惠行为也会出现,以替代对自我利益的完全狭隘的、目光短浅的追求 (Hyden 1990, Oakerson 1993)。
因此,人们并非面对着僵化的选择:将个体行为模式化,一如古典经济学所做的那样;或像另外一种模型所描绘的那样偏爱他人的利益,总是互惠互利。我们需要发展一种不同场域下人类行为的潜在理论,由此,我们可以预测,相对于其他环境,在此种情境下互动的人们是如何获得或失去信任和互惠行为的 (E. Ostrom 1998, 1999; E. Ostrom & Walker 2003; Walker & E. Ostrom 2009)。让许多制度分析学者沮丧的是,我们还没有开发出一个能将每一种情景下个体选择模型化的方法。然而,我们在慢慢地了解情景结构和使用者的多种属性(比如,个体间是否能相互沟通,能否自发地加入或退出,相互了解,获得有关过去行为的信息等等)是如何互动,进而引起互惠和信任成长或恶化的环境的出现(Poteete et al. 2010, ch. 9)。不过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我也鼓励年轻的学者应对这一重要的挑战。
如今,年轻的研究者们有许多挑战性问题需要处理。一些理论和技术仍是适用的,而且会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得到改进。基于更加牢固的研究基础,现在能够从事进一步研究的机会比半个世纪以前更多。我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理由有三:第一,现在,由于美国大学在入学、聘任、年轻教师获得工作任务和终身教职等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制度性变革,妇女和少数族裔学者获得了更多的机会。第二,如今跨学科的学术资助比以前更容易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已经确立了若干项目,用以支持社会科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长期进行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结果的研究。包括《环境保护与社会》(Conservation and Society)、《生态与社会》(Ecology and Society)、《公共事物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ommons)、《经济行为和组织》(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以及《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在内的期刊都具有强烈的跨学科性,并且广受尊重。虽然一些政治学系仍然固执地坚持只有在顶级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才能获得终身教职,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政策也在不断变化,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正在得到认可。我的乐观主义的第三个理由是,人们广泛认识到复杂的制度安排并非自发地含混不清。生态学家和生物学家很久以前就知道,他们在研究由多个层级的不同部分所组成的复杂现象,其挑战在于揭示这种复杂性以便理解它。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挑战是驾驭关于复杂系统的知识(Axelrod & Cohen, 2000),而不是简单地呼吁将其简化。
(作者: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译者:王浦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北京100871)
A Long Polycentric Journey
Elinor Ostrom
[Abstract]In this account, I discuss my own personal journey and the efforts of many of us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 at Indiana University to develop better analyses of how institutions affect behavior and outcomes in diverse settings. First, I reflect on my experience as a young student and in my early career, primarily to encourage those who face obstacles. Then, I discuss our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our research on urban governance and common-pool resources, which helped me to develop more general frameworks for the analysis of complex systems over time. The frameworks have enabled us to dig into and analyze system structure, behavior, and outcomes to make and test coherent predictions and build better theory. Last, I share some ideas concerning future scholarly directions.
[Key words]institutional analysis,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common-pool resources
[Author/Translator]Elinor Ostrom is the first female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and the Arthur Bentley Chair Professor in Indiana University. She is also the common director of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 institute and System,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changes research center;Wang Puqu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Government, Deputy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