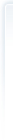
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3.12.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其迁移意愿影响研究”(12CSH03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社会网络视野中的农民工迁移意愿研究”(11YJC840003),2013年度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资助”《新制度学派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研究》(2013 WQ016)。
[摘要]在千里马社区治理的变迁过程中,不同类别的行动主体——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相关商业组织、社区居民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认知,及由此过程中权力关系变化产生的行动策略的“耦合”,共同促使了这一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它的特色之处是回应社区治理技术性问题方面的要求较为主动,回应社区治理制度性问题方面的要求较为被动,这种思路适应了20世纪末到目前为止我国城市社区中社区居民“从单位到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供给需要。但从长期来看,社区内部产生的变化有可能促使该社区治理模式进一步发生组织制度变迁。
[关键词]多重逻辑;社区变迁;行动主体;组织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12-0084-05
一、问题的提出:社区变迁的多重逻辑
当前的社区研究可以大致归为两类,其一是在微观层面来自社区内部的,它从实体论的角度出发,关注的内容大致与社区各种公共事务的管理、及各种公共服务内容的提供有关;其二则是宏观层面的,来自社区外部的,它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关注的核心内容是将“社区”置为我国社会管理的基本社会单元,学者们或多或少基于“单位”到“社区”的宏观历史视角,探讨社区或社区建设、社区转型的目标在于“见微知著”,分析其在社会转型中的典型启示意义。[1]这两种研究取向的第一种,把社区看作是社区居民实现其各种目标的外在环境变量,第二种则把社区看作是外部环境约束下国家实现社会管理、控制的中介手段,某种程度而言,“社区”在此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鲜活意义。
从上述两种基本的研究取向中,可以归纳出社区研究中的规范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简化论”的嫌疑,即理论模型与现实实践存在距离的问题。而组织社会学的近期发展趋势,是志在研究组织变迁过程中“理论模型与实际发生过程中的种种偏差”问题。[2]组织社会学研究的近三十年,对组织的理解经历了从理性系统、自然系统到开放系统的转变。[3]这一转变,也同样适用于对社区及社区变迁的理解。社区不仅仅是社区居民实现其各种目标的外在环境变量,也不仅仅只是外部环境约束下国家实现社会管理、控制的中介手段,社区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它容纳了各个相关层面的行动主体。各个行动主体在其中的相互关系,是我们在中观层面推进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近二十年里,我国的社区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如果能够认识到社区中各个相关层面行动主体的实践逻辑,则有可能还原社区变迁的具体演变过程。这种关注与以往规范研究倾向不同的是,它不再追求社区研究中单一机制解释。它以不同行动主体的多重行动逻辑来理解社区变迁,需要的是还原社区生动面貌的实践研究策略。“强调变迁过程中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旨在解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现象。制度变迁是由占据不同利益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而推动和约束的,而不同群体和个人的行为受其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制约。因此,制度变迁的轨迹和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需要在多重制度逻辑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它们的各自角色,在行动者群体间互动中解读制度逻辑的作用,并关注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过程”。[4]
虽然组织研究的内部仍然存在着种种争论,但是组织研究超出以往对组织内部系统的狭隘关注,将研究视野投注到组织所嵌入的更大的关系系统则是组织研究者所享有的基本共识。制度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如果离开个人所嵌入的更大文化背景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就难以理解个人的偏好和选择,[5]这些思维,为分析社区中各个相关行动主体如何理解周围环境发生的变化,和在周围环境的变化中“抓住机遇”利用权力关系的变化为自身获取利益,提供了相当启发意义。基于此,笔者在下文的分析,将尝试从组织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出发,以社区变迁中的多重逻辑来解释湖北省武汉市一个典型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过程。
二、研究对象、分析策略与社区变迁的不同时期
1.研究对象
目前常住居民达12万人的千里马社区,作为获得中国首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创建文明社区示范点”、“全国城市物业管理优秀示范小区”等60余项国家级奖项的样板型社区,早已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笔者的调研及相关研究的总结,这一社区治理模式不同寻常的治理效果主要体现在[6]:其一,社区各项公共事务管理效果的良好实现,具体体现为该社区社区治安、社区卫生、社区救助、社区管理等,仅体现在社区治安、卫生中的“入住多年以来没有一户居民家中被盗、没有一辆自行车被偷、没有一个人越级上访、没有一起黄赌毒事件、没有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没有一起火灾、没有一名法轮功活动者,无违章搭建、无开窗设点、无占道经营、无油烟扰民、无泥巴路、无牛皮癣式小广告、无居民摘花踩草、道路及两旁绿地无烟头果皮纸屑等”[7]就令人难以置信;其二,以“万家宴”为代表的社区文化的繁荣和以“网格化”为特征的社区志愿者队伍的踊跃,体现了该社区社区建设的突出成效,同其它商品房社区相比较,该社区显然不能用“社区失落论”的观点来看,它确实有滕尼斯所说的古典社区的浓厚味道;其三,社区中各项社区公共服务内容的提供,“涵盖从就业到医疗保健,从文化教育到家庭生活,从婚姻介绍、婚礼操办、小孩接生、幼儿教育到养老百年”[8]等,实现了社区居民在社区中的良好归宿感。
2.分析策略:相关方如何分析目前处境和行动所带来的权力关系变革
在“单位”到“社区”的社会治理转型背景和过程中,社区治理中所涉及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其一、各个相关方如何分析目前所处的环境,换言之,它们是如何理解和认知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组织运作过程的变化(体现为“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这一组织变化给它们带来了何种历史机遇和生活机会,会形成何种“场域”的生态环境?这也涉及到他们如何适应环境和在环境中生存。其二,各个相关方基于对组织变化的认知,是如何创造性的利用这种变化带来的契机,来采取何种行动的?正如克罗齐埃所说“任何孕育着社会深刻突变的危机,都必然要重新碰到一切集体生活中所具有的基本问题:权力问题”,[9]社区模式形成中的权力关系是本文的主要关注。本文所涉及的相关方主要包括: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包括街道和居委会)、商业组织、社区居民等。这些不同的相关方在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历史中并不完全被动,他们“创造性”的运用着他们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理解,并藉此展开行动。
3.四个阶段:社区变迁不同时间节点
在千里马社区治理模式变迁过程的具体分析中,笔者借鉴了尼尔·弗雷格斯坦的策略,[10]他着重探讨了组织变迁的四个阶段:其一、现有策略、结构以及一种给定的权力分配,在阻止组织变迁和促进组织惰性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二、组织场域中的混乱,具有各种利益的行动者以其在组织中的位置为基础,通过这种混乱主张其新策略,并有力量执行和实施这种策略;其三、进入某个已经存在的场域的新组织,为其它组织提供一种榜样的作用;其四、制度化的力量,在这一阶段,某种模式成为同类组织模仿的对象。笔者在研究中关注了该社区治理模式形成过程中四个阶段的具体作用形式和过程,需要说明的是,笔者重点关注的是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因为这两个阶段在千里马社区治理模式历史中的重要性要高于其它二者。
三、千里马社区治理模式中的四个阶段
1.社区治理模式的静默期——积极行动着的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和积极配合着的“单位”
1978年邓小平以对“两个凡是”的破解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并在1992年以“南巡讲话”的方式对国家宏观治理思路加以了确认,这就是经济领域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和政治社会领域制度改革的相对保守变化为典型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在1998年之前,国有企业还未推行大规模改革、福利分房还是城市居民获得住房的主要渠道,“单位制”理所当然的成为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式。
在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作为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的居委会和单位(企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步调基本上是高度协调一致的。居委会和单位在履行社区公共管理职能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的工作上都是积极行动的,它们共同维护着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社会管理的主要目标。在这一时期,社区治理模式基本处于静默之中——单位和社区居民基本不需要也不能够提出任何与当时居委会相左的要求,社区居民在社会利益还未多元化的时期也基本不会对居委会提出任何额外要求。在这一时期社区治理除所涉及的除居委会和单位之外,其它参与的主体和与之对话的主体基本没有,换言之,社区还处于前社区治理阶段——“现有策略、结构以及一种给定的权力分配,在阻止组织变迁和促进组织惰性中具有重要作用”。[11]
2.社区治理模式的萌芽期——积极行动着的商业组织和相对消极的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
1998年发生的重大变革——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全方位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使得社区这一基层组织所面对的“场域”环境不再稳定,从外部环境方面给组织的转型既带来了外在压力,也给组织的转型带来了契机。这也是既有组织研究成果所强调“组织场域外部发生的变化往往成为组织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观点的体现。[12]
“组织场域中的混乱,具有各种利益的行动者以其在组织中的位置为基础,通过这种混乱主张其新策略,并有力量执行和实施这种策略”,[13]在上文所论及的历史背景下,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们面对着相当棘手的问题:其一、周围国有企业中单位制的解体使得大量基层公共事物处于应对无力的状况;其二、上级政府管理者并没有就单位制解体后基层政府管理的改革具体方向和目标做出明确指示——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思路是经济政策迈大步、政治社会政策迈小步,它给整个社会中各个构成部分塑造了一个变革的“底线”,成为各个社会构成部分必须遵循、不能逾矩的“潜规则”,但是对具体能怎么做并没有作出具体说明,一切有赖于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的“摸着石头过河”;其三、宏观政治、社会变革的政策底线的约束决定了他们所能够动员的实际资源相当有限;其四、他们需要与他们的竞争者们——同一城市其它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们——在一个类似于“锦标赛”的科层制晋升体制中争夺其上级管理者“有限注意力”,[14]以获取体系中职务晋升的资本,争取少数晋升的机会。这个问题在城市之间基层政府管理者中间也存在。
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的这些处境决定了他们可能采取的社区管理思路,是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社区管理中的技术性问题——满足居民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等方面的要求,而在社区管理中的制度性问题——从“单位制”到“社区”治理制度及模式的根本转变——则保持相对消极的态度。当然,这一看上去“与外部环境相遵从”的思路并不恒定不变,他们会在社区管理的技术性问题和制度性问题中侧重性的取舍,其基本出发点是如何取得对他们更有利的权力资源和行动主导权,这一特点将在社区模式发展的第三阶段具体说明。
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在千里马社区所采取的这一思路,和同时期其它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的相似思路给予了社区治理模式中其它行动主体——在千里马社区中主要体现为千里马集团,拥有了一定建构性地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机遇,这一时期国内大部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都处于萌发期,具有的共性特征是“高度建构性同时低度秩序化”,给予了其它行动主体更多的实践机遇。
千里马集团在该社区治理模式的萌芽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该集团在千里马小区进行建设之初曾以“某某安居发展工程有限公司”为名,其公司的创始人和高管中有多人拥有在武汉市建委及相关政府部门公务员的经历。千里马集团在社区中的大量经济资源投入,以在社区医疗卫生中甚至以将集团盈利划拨一部分,补贴社区居民医疗经费的超常规举动为典型特征。它远远超出企业物业服务的,对社区居民提供的各种服务,实际上取代了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的相当部分职能。对于当时限于外部环境能够实际动员资源有限的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而言,它有效地缓解了政府有限资源在面对社区大量公共事务和服务中的技术性缺陷,解决了城市居民因环境变化给城市基层政府带来的社区治理中的技术性问题——例如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治安等的压力。此外,它以不需要城市基层政府大量资源投入,尤其是不需要对城市基层政府的组织运行造成制度性变革压力的特征——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区治理中的制度性问题,迅速的取得了城市基层政府的接纳,而不是基层政府的反感和反对。
为什么千里马集团作为一个商业组织会参与到城市基层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来,单纯的追求企业社会价值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得通,特别是对于当时还处于企业草创之初的千里马集团来说。“法团主义可以界定为一种利益表达系统,在其中各种选民单元被组织成独特的、强制的、非竞争的、等级制地排列的、功能分化的、数量有限的类型,这些私利集团类型(即使不是政府创造的)也会得到政府的承认和许可,并且在为了获得他们对选择领导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交易中,以及在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支持方面,被征服赋予他们在各自的组织类型中具有一种深藏不漏的垄断代表权”,[15]考虑到国内房地产行业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千里马集团的组织策略与当地基层政府管理组织行为之间的相互配合似乎更容易得到理解。
对于处于不稳定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国内民营企业来说,获取相关政府部门的庇护,对于它们的商业行为来说,不一定需要理解为经营腐败,这种庇护关系对于企业和其经营活动所涉及的其它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沟通时,能极大程度的减少交易成本,这对于企业的发展壮大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社区治理模式的成长期——积极行动着的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和积极行动着的商业组织
并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组织惰性”完全解释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的所有行为,事实上,它们并不一定总是消极的。在千里马社区治理模式的成长期,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就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态度。这跟它们对社区治理模式的认识,以及从社区治理模式能够获得的利益有关。
在该社区治理模式的萌芽期之后,该社区因其引人瞩目的治理效果逐渐引起了各级政府的关注,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积极行动起来了,参与和逐渐主导了该社区治理模式的总结和阐发——如“三个必到,五个必访”、“4321思想”。城市基层管理者相对于作为商业组织的商业集团而言,更熟悉城市政治话语体系,更能够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阐发业已产生的社区治理效果。例如,在该社区的“交叉任职”模式——“党委成员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社区党委5名成员分别兼任社区各级组织的领导职务,党委书记是BBT集团的董事长,也是BBT社区的居民,党委副书记兼任社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其他党委委员分别是政府职能部门、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成员”[16],就远非单凭商业组织之力可以办到,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踊跃行动着的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
制度环境是分化性的、同时也是竞争性的,即使是处于技术环境中的组织,也可能进行与其制度环境相关的“策略性选择”。[17]千里马社区治理模式中社区治理的基层实践者们与其说是顺应了社会治理的时代潮流和社会潮流,还不如说是在与其上级管理者在共享了一套关于“改革”的底线可以到哪里的基本共识之后,再具体推进社区治理的一系列工作。身处社会管理序列中同一个管理层级的不同城市基层社区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实践工作时,也在相互观望、相互监察,确保他们的工作在顺应社会呼声的同时,没有越出上级政府的底线要求。而这些底线,没有明确的文件规范、指令要求,只能是在实践工作的一次次来回争论中取得“默契”。这里面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在城市基层政府管理中,谁能率先一步抢占“话语”的领先权,在众多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中,即在科层制的政府管理体制中赢取了合法性资本的制高点,诸如“全国城市社区建设试验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市”等制度奖励将会纷至沓来。这种榜样作用不仅能为城市基层政府管理确立合法性,更能为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获取大量政治资本。
同时,千里马集团也从千里马社区治理模式的成功中得到了显而易见的、极其荣耀的政治资本。[18]她领导的开发企业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房地产公司发展壮大成为……20多家全资和合资下属企业,有员工2000多名,年投资额过20亿元,税收名列湖北省民营企业前茅。成为了进入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湖北八家企业之一,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房地产百强”企业、湖北省十大民营企业。可以说,千里马集团与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所共同谋划的“千里马社区治理模式”对其企业组织商业成功的意义是不可否认的,正是因为这一模式在城市基层政府管理中的制度符号性作用,该企业才能够将其原有社区的规模一再扩大,社区居民从无到有,从原来规划的3万人到现在的12万人,再到预期规划的30万人。企业自身也从名不见经传到发展壮大,甚至获取了其它企业难以企及的政治性符号支持。
4.社区治理模式的成熟期?——积极行动着的社区居民
在单位制到社区的组织转型过程中,城市居民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公共事务管理的提供和公共服务的获取。而究竟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何种渠道提供,以何种方式提供,他们暂时无暇顾及,更暂时不具有此种意识。在两者不能兼得需要进行取舍时,他们往往满足于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实现结果而非过程。正是基于此,千里马社区治理模式中的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和千里马集团才以优先解决组织变迁中的技术性问题、而暂时不触及组织变迁中的制度性问题的方式迎合了该社区居民的需要。因此,无论是企业管理者在该社区的发展中精力投入、集团对社区公共医疗的额外经费投入、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的参与,社区居民在面对外部人士的参观考察中有意识的保留,以及部分社区居民对该社区治理模式的真正赞同……都体现了该社区治理模式的成功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有意识的塑造,它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其它商品房社区相比,在满足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方面确实具有独到之处,社区居民对此也是充分配合和支持的。
但是,当该社区治理模式被总结和阐发,并在上一级政府乃至各个部委的肯定批示,甚至部分中央领导的参观、肯定之后,这一社区治理模式即被固定成型,对组织合法性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组织能否适应组织面对的技术性问题的关注。该社区治理模式中制度性问题的缺憾——诸如社区停车费的制定规则和程序、社区居民的自主参与等——则被有意识的选择性的忽略了。与此同时,因为社区规模不断扩大带来的社区居民异质性的增强,和社区居民自主性的不断增强,社区居民并不是总是对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完全被动。一方面,他们选择在该社区中居住即是在考量该社区相比其它社区能够给它们带来的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实际益处;另一方面,他们在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中如果发现缺陷时——例如新近不断发生的社区居民围绕停车位、公共绿地等产生的争端,他们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寻求自身利益目标的实现。相信随着该社区居民异质性不断的增强,居民利益的不断分化,该社区内的各种冲突在短期内还有急剧增长的可能。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社区治理模式的一大特点在于该模式形成的早期,城市基层政府和商业企业作为两种组织系统具有不同的特点。政府组织对制度合法性压力的关注超出了其对技术性问题解决的关注,而商业组织在不触及组织制度变迁的前提下提供了城市居民技术性问题的解决办法,城市基层政府和商业企业在社区中出现了高度的“默契”。那么,在目前因为外部环境变化,尤其是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社区事务自主权的要求等,带来的制度性压力和技术性压力面前,该社区治理模式还能以、还将以何种形式来容纳这些新的变化和要求?我们是把社区居民参与的这些冲突当做该社区治理模式成熟期的正常事务,还是可能给该社区治理模式带来进一步改变的契机,这可能是千里马社区治理模式中的各个行动主体不得不去深思的问题。在该社区治理模式还未能较好解决社区居民的各项权益诉求之前,这一社区治理模式还很难被称为进入了成熟期。
四、简要小结与讨论
从前文分析的情况来看,我们很难说该社区治理模式是在一开始就以明确的目标形式确立了的。我们并不能以某一单独行动主体对该社区治理模式的行动逻辑,来替代该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历史过程或者预测该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前景。该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是该社区中多个行动主体对周围环境的认识,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变化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在该社区治理模式的前三个阶段中,正是城市基层政府管理者、相关商业组织、社区居民这三个独立的行动主体由对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认知及由此逻辑下产生的相关行动的“耦合”而不是冲突,促使了这一典型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
而笔者对于该社区治理模式第四阶段的分析,则提醒相关研究者,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前景,也同样可能取决于以上逻辑。目前,正是社区居民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逻辑,与其它的行动主体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和行动逻辑之间的“不相耦合”,给该社区治理模式带来了冲击。如果该社区治理模式能够以一定程度的变迁方式(部分的亦或是根本的)来容纳社区居民基于自身利益或者社区公共事务争端的利益主张,那么,该社区治理模式或可真正进入稳定的成熟期。同样的推断亦可适用于该社区治理模式的前期,如果在该社区治理模式变迁的前三个阶段,就已经大量出现各个行动主体之间行动逻辑的冲突、争端而不是耦合,那么该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和方向就不会是目前所见之状。笔者在本文中对于社区变迁的多元逻辑和耦合的强调,正是基于此。
笔者认为,千里马社区治理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当组织变迁同时面对着制度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时,该社区治理模式选择了回应社区治理技术性问题方面的要求较为主动,而在回应社区治理制度性问题方面的要求则较为被动。它适应了20世纪末到目前为止我国城市社区中社区居民“从单位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的转变需要,这一转变的显著特征是低度的组织制度性变迁,“制度红利”或者“制度惰性”即是这一社区变迁过程的一体两面。组织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某种制度形式一旦得到支持并固定下来,这种制度就往往会重构自身,构筑屏障防止自己受到外界的影响。在本文所展现的千里马社区治理模式中,组织研究的这些观点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以往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对社区治理的现状多有描述,对社区治理的变迁方向也多有期许,但对社区治理现状如何与社区变迁方向如何连接,则缺乏足够说明,本研究即是力图在这一方面在以往社区组织变迁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本文在探索社区内微观的行动主体与宏观的制度变迁是如何连接的这一问题,亦即社区变迁的具体组织机制方面,存在多个主体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作出了回答。本文也提醒将来的社区研究应该相当的研究关注集中于社区变迁的组织过程机制,只有将这一问题回答清楚,社区以及其它组织形式的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动力机制才有可能阐明,社区研究才会具有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不仅仅是规范意义。
同时,笔者对该社区变迁的解释并不期望建立一个因果模型,这也是组织研究中的一个固有难点。但笔者认为,该社区治理模式虽然在武汉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特色典型,但是与其它国内部分社区治理模式对比而言,可能该社区治理模式中蕴含的不同行动主体多重逻辑的耦合并不是一个孤例,这也有待于相关研究对社区组织过程变迁的进一步推进。
[参考文献]
[Reference]
[1]肖林.“‘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1(4).
Xiao Lin. The “Study of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Studies”: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es on Urban Community in China. Sociological Studies,2011(4).
[2][4]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10(4).
Zhou Xueguang,Ai Yun. Multiple Logic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Towar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0(4).
[3][美]理查德·斯科特.组织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5-89.
W. Richard Scott. Organization Theory.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2. pp5-89.
[5][10][11][12][13][17] [美]保罗·J·迪马吉奥,沃尔特·W·鲍威尔.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26,35,67,134,189.
Paul J. Dimaggio, Walter W. Powell.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p13,p26,p33,p67,p134,p189.
[6][7][8][16]张艳国,胡盛仪,李广平.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中的千里马发展之路——武汉市千里马花园社区调查[J].江汉论坛,2010(6).
Zhang Yanguo, Hu Shengyi, Li Guangping. The Development of Qianlima Community Mod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 Investigation on Qianlima Community. Jianghan Tribune, 2010(6).
[9][法]克罗齐埃.被封锁的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88.
Michel Crozier. Blocked Societ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1989. p88.
[14]周飞舟.锦标赛体制[J].社会学研究,2009(3).
Zhou Feizhou. The Tournament System. Sociological Studies,2009( 3).
[15]Philippe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moratism? in The New Corporatism. eds. By F.B.Pike and T. Smith. Notre Dame Press,1974. pp85-131.
[18]中国杰出女企业家网.社区小总理[EB/OL]. http://www.ccwew.com/news/detail.php?id=5332.
China outstanding woman. The Small Prime Minister of Community. http://www.ccwew.com/news/detail.php?id=5332.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武汉 430074)
Multiple Logic of Community Change
——A Research on Qianlima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in Wuhan
Cao Zhigang
[Abstract]Different types of actors, including local city government manager,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cognition of changes in external environment since 1998, and thus the “coupling” of different subject’s action strategies produced in the cognition of changes in power, commonly generate a particular community governance pattern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anlima Community. Its features are responding to technical problems need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more actively, but responding to system problem demand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more passively, such ideas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whole external environment—“from the unit to the society”,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But changes in internal community are likely to induce to a further organization system change in the long run.
[Key words] multiple logic,community change, action subject, changes in organization system
[Author]Cao Zhig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 Wuhan 430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