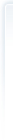
原文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1期139-144页。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英国政策网络理论和治理理论代表人物、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和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R.A.W.罗茨教授在参加2013年2月15日英联邦秘书处研讨会所提交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感谢作者慷慨授予中文翻译版权。
译者:王宇颖,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教授, 厦门361005
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5.11.26
一、引言
关于政策网络已有大量文献存在,其学术地位也经常受到广泛评论( 相关调查和引证参见Rhodes 2006a 和Klijn 2008)。尽管一般读者较少接触到,但其实关于如何管理网络的文献数量亦在增长( 例如参见Agranoff 2007;Kickert, Klijn和Koppenjan 1997;Goldsmith 和Eggers,2004)。本文不在于增加本已过多的理论文献,也非针对“运作中”的网络的又一案例研究,而是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解释和提炼,形成对从业者行之有效的经验。
二、什么是政策网络?
关于网络的分析有多种表现形式,存在于各社会科学学科中。本文侧重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中最常见的一类网络分析—— 政策网络分析。社会科学各学科几乎无法就某个概念的含义达成共识。所以,在各种关于政府与其他国家行动者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和依赖的概念中,政策网络只是其中之一,其他概念还包括议题网络、铁三角、政策子系统,政策社群,认知共同体。这些概念通常在联系的紧密程度上有所不同,议题网络较为松散而政策社群成员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此,我重点讨论“政策网络”,并将其定义为:
政府和其他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一系列正式制度性联系以及非正式联系,如果不懈地进行磋商的话,这些联系基于公共决策和政策执行的共同理念和利益而形成。
政策网络中的行为如同游戏中的行为,以信任为基础,必须遵守由网络参与者磋商后达成共识的游戏规则。因为在资源分配和行动者的议价技巧方面存在差别,所以网络产出的结果以及网络与网络之间也有所不同。行动者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政策由此产生。这样的网络在相当程度上享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自治。
网络可以自下而上发展起来,也可由中心机构建立。两种方式产生的网络通常都在官僚制影响下运作,因为它们依赖于中心机构获取资源。然而,网络有自己的鲜明特征,表1对提供服务的三种主要途径做了简单比较。
网络是一种独特的协调机制,也是一种不同于市场和官僚制的治理结构,因为其核心的协调机制是信任,如同命令是官僚制的重要机制,价格和竞争是市场的重要机制一样。在合作行为中,信任不可或缺,它同时也是网络赖以存在的基础。信任是网络的一种属性,网络的特征还包括外交和互惠。
(一)信任
网络和外交型管理的核心概念都是信任,信任是“网络运作中最重要的属性”,是核心协调机制(参见Kramer and Tyler 1996)。共同价值观和规范使复杂的各种关系得以黏合,信任对于合作来说必不可少,因此,信任也是网络得以存在的基础。同时,信任是不可计算的。如Powell(1996:63)所言,信任“既非出于选择,也非被植入的,而是被学会和被加强的,因此是持续的互动和讨论的产物”。所以,维护信任是一项相互的、无止境的任务。Fox(1974:362)对劳资关系中的信任做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网络。因此,在信任度高的网络里,参与者共享某些目的或价值;对对方充满长期责任感;彼此提供自发性的支持,不会狭隘地计算成本或期待短期内获得同等回报;自由坦诚地沟通;将自己的命运交付对方;绝对相信对方的信誉或动机。
(二)互惠
网络涉及到友谊、忠诚,甚至利他主义(Thompson 1993:54-8),但最重要的是,网络文化的特点是互惠性。正如Powell(1991:272-3)所说,互惠根植于“维持交换的规范化标准”,尤其根植于受惠、义务以及长期性。因此,缺乏对等性交换会产生道德上的制裁,契约使得各方保持联系,回报是一种长期性的关系。然而,正如Thompson(1993: 58)所述,互惠也是一种象征性关系,“在不断交换的过程中,深层次的义务和责任得以建立,象征性状态得以确认,隐喻的社会性参照产生了。通过这种方式,网络的协调性变得稳定。
(三)外交
外交是指通过协商来进行管理。外交家必须说服“其他政府接受,实际上可能是帮助推进该外交家所倡导的政策”。主要技巧是“坚持不懈地劝说在变化中保持秩序”(Watson 1982:125 and 223)。Nicholson(1950:15)把外交定义为“通过沟通来管理国际事务”。尽管这听起来有些老套甚至古朴,但是Nicholson传递了一个转变语言风格的重要信号,强调要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帮助他人实现目标。
外交可能是一个老式的字眼,但沟通和说服的艺术并不局限于外交。如前英国公务员局局长Douglas Wass先生所说:“技巧和外交是公共服务的基本要素”(Hennessy, 1989:150)。公务员已经管理网络多年,但他们要么选择避而不谈要么浑然不知。这个理念其实不是新的,尽管看起来富有新意,其实只是暂时被遗弃。外交,信任和互惠这些字眼是网络管理的核心。
三、网络何时成功?
当市场和官僚制失灵的时候,网络得以发展。这时,组织之间的关系以信任和互惠为特点,管理即沟通,而非命令,这从表1中可以明显看出。此外,与任何其他形式的公共部门管理相同,网络取得成功还依赖于相关信息、技能和资源。当行动者隐藏信息和资源,实际上就是拒绝分享信息和资源时,网络所赖以存在的合作不可能实现。现有的文献还规定了关乎网络发展的其他一些更具体的条件(见表2)。
换句话说,当服务的提供需要合作、去政治化、专业化、本地化和量身定制时,网络将取得成功。
四、网络何时失灵?
网络,如同所有其他的资源分配机制一样,要付出成本。制度缺失(institutional void)很难处理。网络难以驾驭——它已被比喻为放牧一群猫,或拉动橡胶杆,这是一个耗时、缓慢的过程,因为网络治理规则而变得更加复杂,即,组合的管理,多只手的问题,对协调的追求以及当地所有权。
(一)组合的管理(竞争与合作)
网络很难与其他手段结合起来提供服务。市场化的一个明显影响是,它破坏了网络的有效性。这里的意思并不表示网络是行不通的,所有治理结构都会失灵。政府必须找到合适的组合,因为不同机制可能无法融为一体。竞争与合作是一对不稳定的伙伴。政府推动竞争和外包,其结果是“损害……共同的价值观和承诺”以及“营造不信任的氛围”。市场关系“损害了建立在合作互惠和相互依存之上的专业化网络” (Flynn, Williams et al. 1996:115 and 136-7)。总之,合同破坏信任、互惠、非正式化以及合作。
人们借用民俗理论来处理合作和竞争风格之间的冲突,他们吸取之前的当地工作经验(见下文)。他们可以在这种混合的情境下生存。他们估算哪种服务提供机制在哪种情境下可行。不过还是普遍遇到了困境。人们会错误估计哪个信息应该发送给哪些行动者,或者这个信息适合哪种场合。人们恼怒而由衷地发出“其他机构能不能像我们这样”的要求,这体现出他们的受挫感。
(二)多只手的问题(问责与效率)
Bovens(1998, 46)指出,“多只手的问题”就是,在复杂的组织中,大家共同承担政策责任,因此很难找出究竟是谁的责任。他还指出,碎片化、市场化以及因此产生的网络带来了新的“多只手的问题”(Bovens 1998, 229)。在一个网络里,每个组织可能都有相关官员和政治家来承担责任,但是谁为这些组织整体上负责呢?绩效指标可能会提高效率,但在多个机构的情况下,更可能出现推诿扯皮的情况,因为责任被分担了,受中心机构的管制也大大减少了(Mulgan 2003, 211-14)。多头责任导致重复、部分重叠和效率低下,削弱了中心机构控制,并使网络中的成员产生“你又不是我老爸”的反应(Mulgan 2003, 225)。
(三)对协调的追求(控制与相互调适)
协调有一个核心宗旨。协调的倡导者通过将一种新的管理风格强加给其他机构来实现对各部门及其他机构的协调——无论是中央机构、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无论是公共或私人部门。一项命令不管如何粉饰,永远面临遭到主要行动者抵制的风险,并且在处理地方性事务时,缺乏灵活性。不断地稍稍施加压力终究还是一种外柔内刚的命令。当位于金字塔顶部的人看不见底部的情况时,很可能出现的意外后果就是失控。
尽管西欧各国面临着被要求更频繁、更积极地进行协调的强大压力,中央政府在采取协调活动方面仍然保持低调。据Wright 和Hayward (2000: 33)的观点,协调是非常消极的,它建立在强大的部委之间持续分离、相互回避和减少摩擦的基础上。协调位于国家机器的较低层次;由具体、稳定的网络来进行组织;很少有战略性;是间歇性和选择性的;在政策过程后期临时上马、具有政治色彩、以问题为导向及反应式的。总之,协调是现代政府的点金石,一直被追求,但始终得不到,这往往因为它是建立在对目标和协调者已达成一致的假设之上(Seidman 1975:190)。网络成员抱怨道:“你无法和紧握的拳头握手”。
但是,协调并不局限于中心机构利用规则来进行协调,还有其他方式。Lindblom(1965)分析党派相互调适的那本著作是一本经典却常常被忽略的关于非正式协调的书。每个派系成员所做的决定都服务于自己的目标。决策者要么只是迎合周围人的决定,要么诱使其他决策者改变,这时相互调适就产生了。中心权威决策者是不存在的。相反,每个决策者使用诸如讨价还价、互利互惠、操纵和赔偿等方法,试图诱使他人做出调整(同样参见Chisholm 1989),这与外交概念明显有着不可避免的部分重叠。
(四)所有权(战略引导与地方灵活性)
冲突有多种形式,主要有:个人与组织承诺的冲突、地方与国家层面的公众期望冲突、当地的灵活性与国家法规的冲突以及网络目标与国家调控的冲突。当地方性网络受到中央操纵或指导时,就不再是地方性网络了。实际上,当对网络进行中央管理时,横向关系转换成垂直关系。中心机构不得不比较达成共识和强制命令的成本哪个更大,这时往往认为是后者。这种关系叫做正式协商,至少这种说法不牵涉到地方自由裁量权。两难之处介于采用收还是放的干预方式,介于战略引导和地方灵活性的把握。中心机构可以采用权力下放的协商方式,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来换取一致。这种放权式管理需要为网络的工作设定范围,但是又要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中心机构要进行自我否定是非常困难的。网络成员尖刻地说道:“他们是只说不做的”。
五、中心机构如何管理网络?
网络管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观点,即,中心机构对网络管理采取干涉。中心机构面临两项任务:管理整体网络以及管理各个独立网络。
中心机构是网络的节点。中心机构一词通常指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当局。这些“中心机构”都属于一系列网络、企图管理一系列网络,即“由多个网络形成的整体网络”(Ysa和Esteve 2013; 可参见Wassmer 2010的相关文献综述)。管理整体网络具有独特的挑战,最显而易见的是要找出该机构试图管理的网络有哪些。机构往往不知道哪些是自己的网络,更别说其他机构的网络了。没有机制来协调中心机构对整体网络或个体网络所做的回应(关于管理整体网络工具的综述参见Heimericks等人,2009)。
如果中心机构将网络当作工具,那么网络管理手段可分为三大类: 工具手段,包括奖励、制裁和对网络进行微观管理;互动手段,包括沟通和外交;制度手段,就是指中心机构改变游戏规则,即为网络活动设定界限(参见Kickert et al 1997)。“十条戒律”列表结合了这些不同类型的手段(见表3)。Perri等人(2002:130)曾指出,网络管理“不是关于火箭的科学”,用不着那么精密,该表体现了他们的这一观点。
和表2、表3中列出的具体原则和规定同样重要的,是蕴含其中的理念: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组织凝聚力、游戏规则、合作型领导以及叙述故事。
(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从关于执行和基层官僚的研究中我们得知,自上而下的举措常常失败。自上而下的执行模式把政府的既定政策目标作为出发点,并检查它们为什么没有成功(例如Pressman and Wildavsky 1984)。失败是由于多个机构参与其中,且缺乏服从和理解,从而导致目标不统一。由中心机构进行监督、监管和给予更多的指导
基本上是治标不治本,往往收效甚微。自下而上的观点则不同,这种观点强调政策执行是靠基层官僚的行动来调节的,他们的视角反映了当地的实际条件、当地的情况和他们的技术专长。例如,Lipsky(1979: xii)就认为,“基层官僚所做决策、所建立的例程以及他们创造出用以应付不确定性和工作压力的策略,有效地变成他们所执行的公共政策”。本文关于网络的论述不言自明:网络无疑是杂乱、无固定章法可循的,中心机构可能以介入,但无法控制。
(二)组织凝聚力
组织凝聚力与许多其他概念有相同之处,如职业文化、制度性记忆和行政文化。这些概念有一个共同观点,即,组织里的成员所传承下来的信仰和实践形成了组织的凝聚力。网络也不例外,一个明显的情况是,成立不久的网络所拥有的这种传承很少甚至没有,所以组织凝聚力很小。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加强组织凝聚力。首先,网络领导者可以用其他网络成员的经验作为框架来叙事(见下文)。其次,网络活动可以产生共享的经验。根据从易到难的顺序排列,网络成员可以共享信息、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进行战略规划、联合提供服务和实现资源共享。可行的就是最好的,因为“速赢”——比如成功的合资——能够满足成员的期望、建立信任并强化网络行为。
(三)游戏规则
很多网络都是在官僚制的影响下运作,也就是说,它们依赖中心机构获得合法权威和财政资源,但在执行政策时又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反过来,因为网络包括了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所以能为中心机构提供更多的资源,是联系公民社会的桥梁。中心机构的作用是为网络的行为设定界限,例如做好战略规划。关于战略规划的问题在于,它可能因为篇幅冗长、过于详细的规定、众多的绩效指标成为网络的沉重负担——当情况发生变化时,这些都不起作用了。战略规划不必如此,比如,英国政府的一位高级部长就只是把部门的战略规划潦草地写在一张A4纸上,他的战略规划只是为该部门设立路标,而不是一张布满了街道名称的地图。
(四)合作型领导
Ansell和Gash(2008, 544)把协同治理定义为集体决策过程,“其中一个或多个公共机构在正式的、共识导向的和协商式的公共政策执行或公共项目管理中,让非国家的利益相关者直接参加进来”。关键问题是,对立的利益相关者能否在工作中进行合作?答案是“有保留的肯定回答”,关键是领导,在设定和维护明确的基本规则、建立信任、促进对话及争取共赢等方面,领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Ansell and Gash 2008, 12–13)。对于这种类型的领导有各种描述:放权型领导、软性领导、综合型领导、催化型领导或外交型领导。作为地方主办者的领导者所要做的就是建立网络。Stoker(2004:139)认为,领导者的任务是“帮助各个社区表达意见、消除分歧、发展共同愿景并建立伙伴关系,以确保取得成果”。领导不是控制,而是支持他人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
(五)讲故事
合作型领导的“艺术”是讲故事,它作为一种工具,越来越受到管理者的认同。因此,商业研究文献把领导看作“对意义的管理”,是领导者“向追随者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是“教育、启发、灌输和说服”(Shamir et al 2005: 14 and 15)。领导是“一种互动形式的社会建构”,有效的领导“很大程度上基于对他人经验的编排”,其中,“语言、仪式、戏剧、故事、神话和象征性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Smircich and Morgan 1982: 258 and 262)。而种种见解通过管理高层所叙述的故事,转化为整个组织的实际经验(例如Denning 2004; Rhodes 2011)。因此,合作型的网络建设和管理的领导者所起到的一个重要催化作用,就是编排关于我们在做什么及我们为什么这样做的共同故事。
六、结论:合理推论
政治学家的预测常常不准确,但我们可以追求“合理推论”,即笼统的陈述,陈述的合理性来源于有充分理由,而理由充分则因为是从相关信息中推理出来的(转述自Boudon 1993)。表4汇总了支撑推论的相关信息,是对前文的总结。
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哪些具体推论?有五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1.网络不是中心机构用以实现自身中心目标的工具,网络的优点在于相对于中心机构的独立性。
2.中心机构可以通过减少对整体网络管理的干涉、培养合作型领导者及提供技术支持,来帮助建设和管理网络。
3.中心机构可以设定战略性路标,为地方网络的行动设定宽泛的界限,以确保网络在官僚制的影响下运作。
4.合作型领导需要外交技巧和讲故事的艺术。
5.网络的目标是创造组织凝聚力,从信息共享、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联合提供服务一直到资源共享,从而确保网络的未来。
但是,网络是杂乱的,无法确保成功的结果,只有来自网络治理规则的残酷压力和不断培育网络的迫切需要。更新一下Franois de Callierès的观点就是,网络领导者,无论产生于中心机构或是网络成员,都需要换位思考。Clifford Geertz(1973:9)认为,文化人类学是阐述“针对别人关于他们自己及同伴在做什么的解释,我们做出我们自己的解释”。想要成为网络管理者的人应该是成长中的人类学家,战略性地讲故事的人必须了解和分享别人的故事,来创造网络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