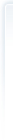作者: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向淼,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310058
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6.08.01
公共行政应采纳古德诺在1886年所倡导的法律主义模式,还是40年后怀特所强调的管理主义模式,学界为此争论了近一个世纪。[1]自西蒙与沃尔多开始,持续的争论皆聚焦于作为政治科学的行政、作为管理学的行政和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公共行政,[2]从而只见“行政科学还是政治哲学”之辩,[3]忽略了法律的面向。直到1983年,罗森布鲁姆在《公共行政评论》上撰文,明确将公共行政的法律与政治渊源区分开来并将公共行政的渊源表述为管理、政治与法律三种路径,挑战了上述关于公共行政学是“行政科学还是政治哲学”之争的传统认知。[4]这一挑战的背景、结果与意义,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关切。这种关切在法与行政间关系的大背景下使本文具有了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法律与公共行政的关系从紧张趋于和缓、从分离走向整合的演变历程,另一条线索是公共行政学从传统的政治与行政二分观念转向管理、政治与法律三维分析路径的当代形态与意义。
一、渊源:行政法与行政学的早期分化
在19世纪中后期社会科学的制度化进程中,德国的罗化斯·冯·史坦首次在《行政学》一书中将广义的行政研究区分为行政法和行政政策学两个门类:前者着重于行政权的合法性,后者侧重行政的合目的性。[5]这预示着行政法与行政学日后的分化:与行政法兴起于欧洲大陆不同,行政学虽然起源于欧洲大陆,作为科学的行政学却正式形成于美国。
公法的兴起,市民法治国的出现,权力分立学说的通识化,对基本权利保障的信仰和国家不干预的经济学教条,要求立法权和司法权加强对王权的限制,推动欧洲从绝对主义开明专制向自由主义法治国转变,强调国家行为必须服从法律,从而在欧洲形成了行政研究的公法路径。[6]法律实证主义要求以实证法为素材、围绕法律规范构建抽象化的逻辑体系并广泛排除法律之外的政治、经济、历史等因素,使行政法学成为一门独立、规范的法律科学。经德国行政法鼻祖奥托·迈耶之手,以“法律保留——行政处分——行政救济”为主要建构体系的行政行为形式理论逐渐演变成为整个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体系,形成了由议会立法和司法审查制约行政权的控权模式。
行政法兴起于欧洲,行政的政治科学路径即公共行政学却形成于美国。威尔逊对此有着并不准确的解释:与欧洲大陆处于垄断地位的国家和公共权力必须不断改善行政(统治)方法不同,英国和美国没有限制、监督和改进行政权的紧迫性,因而长久以来欠缺一门旨在发展行政管理、改进政府组织的行政科学。[7]实际情况可能与威尔逊预设欧洲有发达的行政科学相反,欧洲大陆限制和监督权力的紧迫性超过了改进行政管理的需要,行政法的发展由此掩盖了行政学本身的进展,导致行政学在欧洲“步入了长达百年以上的沉沦期”。[8]据陈新民教授观察,德国的大学直到二战后受美国影响才开始成立政治系并以行政学为主要科目,发展速度极慢。换言之,19世纪末,不仅英美国家欠缺行政科学(像威尔逊所认为的那样),欧洲大陆事实上也只有以国家学说为核心的官房学、警察学传统而无行政科学。[9]在城市发展和市政研究兴起的背景下,倒是威尔逊对亟待加强行政管理的敏锐洞察,使美国成了行政科学研究的大本营,他本人也因此被称为“行政学之父”。此后,以威尔逊、古德诺和古力克的贡献为开端,管理、科学和效率成为公共行政学的基本底色。
限制行政专权与强化行政管理之间的张力,推动了行政法学和公共行政学的分化。法治国理想中的行政法学采“规范-控权”取向,以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目标,强调司法审查、程序控制与权利救济。公共行政学采“管理-效率”取向,强调效率和经济原则并形成了以组织、人事、预算、决策以及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为核心的内容体系。至此,行政法学与公共行政学除共享“行政”二字外,在核心目标、理论进路、基本原则、研究范式等方面已无共通之处。
不过,美国的古典公共行政学仍然呈现出受到欧洲公法传统影响的痕迹,早期公共行政学家和政治学家往往也是(甚至首先是)行政法学家。威尔逊与古德诺均受过法学教育并任法学教授,威尔逊所著《行政之研究》的主题涵盖了宪法、政治学与行政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而古德诺的《比较行政法》和《政治与行政》分别是行政法和行政学领域的代表作。威尔逊认为“公共行政就是公法的明细而系统的执行活动”,古德诺将行政的功能区分为司法行政和执行法律以及建立、维持和发展政府组织的功能,执行法律的功能又可以称为“执行的功能、准司法的功能、统计的和半科学的功能”。[10]由此可见,公法因素与管理因素并存于早期公共行政学之中,这也构成了行政法与行政学分化之后、公共行政学内部的公法模式与管理科学模式冲突的源头。
二、矛盾:公共行政的“去法化”与行政法的“去行政学化”
行政的公法路径强调政府是国家统治权的主体并奉宪法为当然基础,认为行政国家是公法、法律和法律文化的产物,且政府管理有别于市场管理,对政府官员的政治问责也与面向市场主体的绩效奖金截然不同。[11]但实践领域的发展大大超出了公法路径的预期:运用社会科学改造古典自由主义国家的政治与政府结构以满足大规模行政任务的需要,导致公共行政的管理科学模式——认为行政国家是管理主义文化的胜利,批评法律对行政管理形成了掣肘——逐渐兴起。因此,虽然怀特十分重视法律,但因基于管理主义的市政研究在上世纪20年代形成体系并蔚为一时风气,他也只能强调从法律之外的管理视角来思考行政问题。[12]
不过,公共行政管理科学模式的首要敌人还不是公法模式,而是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中的政治价值。19世纪下半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展要求政府非政治化,为公共行政与政治相分离、成为一个摆脱法律与政治价值而采管理科学模式的独立领域提供了合法性。与此相对,对行政之管理主义科学化取向的过度强调又引发了对忽视公平等政治价值的疑虑。西蒙基于逻辑实证主义区分决策中的事实要素与价值要素,致力于建立仅关心事实叙述并奉效率为根本准则的管理科学,[13]沃尔多则否认这种纯粹事实决策领域存在的可能性,认为对效率价值中立的过分强调以及将效率与民主相对立构成了民主行政的最大障碍。以西蒙和沃尔多之争为开端,举凡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诸理论流派,都围绕着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效率与公共性进行论辩:一方竭力摆脱政治价值并强调行政的管理主义科学化取向,另一方则试图重新将政治价值植入公共行政并以此矫正其管理主义倾向。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观念的“阴影”下,围绕公共行政学科性质的讨论局限于互为敌手的“行政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
因此,对于公共行政的公法基础,论者要么选择性地将它们遗忘(认为管理主义取向的行政科学与法律无关),要么基于法律与政治价值的共通而牵强地把它们混同起来(认为植入政治价值就代表着强调其公法渊源)。以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为例,虽然他强调“有效的公共行政管理者必须具备宪法上和法院对宪法的解释上都牢不可破的背景基础”,[14]但民主行政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仍然是对政治价值而非法律的关注。也就是说,尽管公共行政在一般意义上奉宪政为根本价值,但公法在行政科学时代显然已成为被遗忘的传统,法律本身并不在公共行政学的具体考量之列。究其根源,“行政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而行政法学是应然的科学”。[15]公共行政与法律在“是”与“应当”之间形成了巨大鸿沟,早期公共行政学内部并存的公法因素与管理因素就此演变为公共行政学之公法模式和管理科学模式的对立:行政管理者对法律尤其是诉讼带来的责任甚为不安,要求规范和限制行政权的法律也离真实的公共行政实践越来越远。
一方面,对行政官员来说,法律尤其是广泛的程序要求不仅限制任意的自由裁量权,还会形成寒蝉效应并加重行政负担、威胁行政效率、阻碍行政决策。法学显得过于规范化,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总是“以某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法律”,[16]因而受到作为社会科学大本营成员的政治科学的排斥就不足为奇。对法律的敌意见诸美国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不需一一列举。沃尔多就曾有略显尖刻的批评,“(只要对文献稍有涉猎,就会发现)如果说有人在这种新秩序中无足轻重的话,那就是法律人。他们社会形象低微,与新管理主义的精神格格不入,代表一切令人厌烦乏味的事物”。[17]林恩(Laurence E. Lynn Jr.)更为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敌意的根源:美国行政国家的发展需要强调经济、效率、效能等价值,不仅科学主义的信念要求公共行政学与其他学科划清界线从而确立学科自身的合法性,而且常规公共行政也不需要作为专业知识的法律出场,这导致美国的公共行政学拒斥欧洲的形式主义法治框架而接受了“行政就是商业”(administration is business)的教条,并形成了持久的“反法律”倾向(anti-law temper)。[18]
另一方面,以规范行政权力、保护个体权利为目标的法律不重视成本效能的考量,在控制行政裁量权之余已无法触及真实的公共行政。以法学方法论为基调的行政法学过于强调自身的完整性,“是在缺乏同行政学的联系中发展而来的”。[19]实证主义的法律观认为,法律要充分发挥综合性的社会功能,就需要构筑一种便于法官解释和适用的、可通过逻辑演绎得出结论的、客观中立的规范体系——正是这种认为法律在逻辑上自洽并可进一步予以科学化的信念,将法律当作对行政的控制和问责规范而非授权机制,构成了公共行政的最大敌人。例如,在法律人看来,新公共管理对计算、市场和契约的冷酷强调显然与行政法的程序主义和基于宪法的人权与公民权利相冲突。[20]因而,行政法并不关心行政官员事实上做了什么,接受法教义学或普通法训练的法律人也难以真正理解良好行政的重要性,形成了“忽视行政”的恶性循环。“检视那些法律论著的目录就会发现,本是政府重要部分的行政,在书中要么完全不被提及,要么仅以几个段落草草带过”,[21]行政法的“去行政学化”由此可见一斑。
在公共行政学围绕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争论的长久拉据战中,各方都聚焦于行政的某个单向度特征而忽视了行政与法律的交融以及政治价值与法律视角的区分。无论是行政科学还是政治哲学路径,都对法律路径相对独立于二者的特殊性质视而不见。然而,法律事实上既是沟通政治与行政的媒介,又具有与它们相区别的价值取向。在实践层面,如果说法律的上游输入端涉及国家或社会意志的形成,那么作为下游输出端的司法裁判则深深卷入了对行政过程和行政效果的考量之中。作为变动的政治权力格局中的角色扮演者,法院不仅要求公共行政恪守宪政价值,而且不断向公共行政输入法院自身在特定背景下的价值判断,从而发挥着广泛的政治与政策功能。在学理层面,作为一个领域,法律是公共行政当然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公共行政的一种经典定义就是“执行法律”。[22]与沃尔多认为效率并非管理的核心价值相似,罗森布鲁姆等认为,管理既非公共行政的全部,也不是其核心功能,公共行政除管理之外的其他内容要交给行政法去处理。[23]基于对法律与政治和管理的区分,罗森布鲁姆创造性地提出,公共行政在政治与管理视角之外还有第三种面向:法律路径。法律路径为公共行政提供了不同于经济、效率、效能或者代表性、回应性、政治问责的合法性基础,在组织结构、认知途径、预算、决策等各方面都有着不同于政治与管理路径的独特视角。因而,公共行政管理者是“管理者、决策者”,也可以且应该是“精通宪法者”。[24]
如果说行政国家的兴起促进了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倾向,那么从行政国家到宪政国家的转型则使得法律路径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发挥了巨大影响。行政法与公共行政学从分离走向整合,作为古典公共行政学形成基础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观念也转向了公共行政“管理、政治与法律”的三维分析路径。随着公共行政与法律学科间的对立淡化,公共行政学内部的范式冲突也得以缓解。
三、整合:从二分法到三维分析路径的转变
如前所述,公法传统似乎久已被公共行政学界所遗忘。不过,在管理科学模式主导着公共行政的前进方向之际,仍然不时会出现“重弹老调”的呼声。即便经立法者授权的公共行政为实现有效行政需要借助一系列技术工具和组织管理方式来对法律所设定的多元价值进行政策式的权衡折衷,但宪政民主制度不仅要求有效行政,也要求合法行政。公共行政官员必须依法律——作为“将民主通过宪法过程贯彻到具体政策的途径”[25]——行政,不关注法律的行政将意味着混乱而非效率。就行政国家的发展而论,对“行政集权的科学逻辑”[26]的过度强调带来了大量问题并要求从外部监督行政,向宪法国家转型就需要宪法和法律在公共行政领域再度登场。
与此同时,与古典自由主义相适应、强调单向控制机制的行政法也遭遇了危机。源于社会实证主义、社会进化论与实用主义哲学的行政法的功能主义进路,[27]关注行政权的实际运作,强调政府的社会功能,将法律视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保障机制,力图把行政法真正确立为“有关行政的法”。[28]法社会学家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将法律分为压制型法、自治型法与回应型法,其中,回应型法既是一种社会变革的法制模式,又是一种法制变革的政策模式,能够统合法律权威、法律秩序和社会公认价值,回应社会需求并促进自身的修正和完善。[29]公共行政需要宪法和法律再度出场,而功能主义视角也要求法律关注社会事实、回应行政实践。
在现代公共行政需要法律监督、传统行政法遭遇危机的双重背景下,法律与公共行政的关系从紧张趋于和缓,从分离走向整合:一方面,法律以其独特品性塑造着公共行政从而推动公共行政法治化;另一方面,公共行政对成本效能的考量也大规模地渗透进传统的法律领域。这一相互融合的进程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宪法与行政法的实质性变革。“法律正是对公共行政转型,使其融入美国宪政政府的一个工具。”[30]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贯穿美国公共行政学史并可追溯至建国者们对联邦政治与政府制度的宪法构想。美国行政权这个“最危险的分支”扩张所形成的宪法危机也引发了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由此强调从官僚制行政转向民主制行政,确保公共行政立基于宪政和法治秩序。[31]通过明确赋予个人新的宪法权利、扩展起诉权概念的范围、响应前瞻性和补救性的法律诉讼、以有限豁免责任原则替代绝对豁免原则等行动,法院对公共行政施加了广泛的宪法制约并将宪法价值输入行政管理者的思维之中,使公共行政获得了宪法的形式。[32]作为宪法的具体化,古典自由主义控权取向的行政法也在不断变革:[33]无论是行政程序立法的突破和创新,还是“传送带模式”向“利益代表模式”的转型,以及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强调,都构成了在新的条件下促使公共行政合法、有效运作的实质基础。继斯帕索和特里1993年在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公共行政与宪法”特刊中发文首创“宪法学派”之后,2007年,理查德·格林、凯伦·哈特、斯蒂芬妮·纽博德、罗尔、罗森布鲁姆等人正式发起“公共行政的宪法学派”运动,致力于挖掘公共行政的公法传统并进一步理解宪法和法治对公共行政的影响。[34]
二是司法审查变迁与“新伙伴关系”的形成。行政权不仅要受议会立法的约束,还要接受司法权的监督。首先,法院并不愿意成为行政管理的“橡皮图章”,其对公共行政的审查影响到行政裁决、政策制定、信息发布等一系列行政职能,因而行政官僚通常认为司法审查容易对行政产生钳制作用,认真对待法院的裁判哲学已成为行政管理培训的重要内容。同时,现代法院在发挥监督功能的同时,往往也要考虑多中心的目标,不仅日益对行政官僚所面临的时间、程序等资源和要求尤其是财政等约束条件更加敏感,而且在诸多情况下为行政裁量提供合法性依据。[35]在实践中,自谢弗林判例之后,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否则法院在一般情况下应尊重行政机关的政策性决定。其次,社会生活的快速变迁与法律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往往促使法院在教育、环保、医疗、交通、贸易乃至同性恋、枪支管理等充满价值和意识形态分歧的领域从“补充立法”的传统角色转变为“法官造法”的急先锋,从规制的审查者转变为政策的制定者,在公共行政领域发挥着广泛的法律政策功能。法院要在监督行政与尊重行政的合理决定之间取得平衡,甚至与行政协作而成为现代公共行政的重要参与者和决定者,行政机关与法院已结成“新伙伴关系”(New Partnership)。[36]
三是新行政法与治理的兴起。新公共管理对经济、效率和效能的强调,“全国绩效评估运动”对以放松管制、顾客导向、员工授权、服务外包为特征的政府再造的青睐,公共行政的变迁使传统行政法在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等方面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37]带有政策和效益考量的各种新行政法比如政府规制理论、面向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行政法政策学、功能视角中的行政法、行政过程论、转型行政法学等开始涌现。[38]公私部门间的界线被打破,公法与私法交织渗透,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新视野和新脸谱甚至引发了“究竟是市场需要法律的控制还是市场本身就是法治的一种新形式”[39]的追问。作为对福利国家危机和全球化挑战的回应,强调去中心化、多中心、多层次与多种工具并存的治理理论跨越了政治、行政与法律等不同的社会科学门类,[40]并在行政法领域形成了“第三条道路”的愿景:超越管制与解除管制、法律指令与自发市场行为的概念二分法,为统一经济效率、民主合法性与社会公平而寻求一种可持续的结构和开放的框架。[41]这种愿景,正体现了法律与行政融合的趋势。
现代公共行政常常要求复合主体参与和多种治理工具并存,法律与公共行政的关系超越了前述“行政需要法律出场”或“法律应该回应行政实践”的单一层面,走向了深度整合与交织互动。美国联邦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戴维·贝兹隆1976年首次提出法院与行政的“新伙伴关系”并把法院当作行政的“资深合伙人”(senior partner),[42]罗森布鲁姆进而发现法院在这种新伙伴关系之中不断强化着自身在行政国家中的权力。在1985年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法律与公共事务”特刊中,R·谢普·梅尔尼克认为司法对规制项目的干预使法院卷入了由法院、规制机构、议会小组委员会和利益集团构成的多头政治联盟及其塑造的行政过程之中,[43]廷斯莱·E·亚布洛也强调判决结果及其执行实际上仍是包括行政机构在内的多元主体间互动、妥协的结果(尽管法院对行政事项的干预构成了改革的催化剂)。[44]进入20世纪90年代,查尔斯·怀斯与罗斯玛丽·奥利里重新界定了法院与行政间的“新伙伴关系”,认为它已由法院与行政的合作、法院对行政的篡权演变为包括司法、行政以及立法者在内的“新三头统治”(New Triumvirate)。[45]可见,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法院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以及法律与行政的关系呈现出进一步复杂化的趋势。
总之,法律与行政的综合视角强调多元价值的整合与合作,核心议题是运用合适的法治设计和正当性原则,确保更具效率、效益、合法、稳定的公共行政。[46]如上所述,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治理已经体现出法律与行政动态整合的前景。在治理框架下,卢曼的功能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既强调行政法规范的封闭性,又保持行政法对行政认知的开放性,从而以一种内部视角处理公共行政和行政法关系的可能性。[47]此外,在规范主义的“红灯理论”与功能主义的“绿灯理论”之间寻求共识,追求法官、立法者与行政官僚的有效合作,支持行政官员通过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参与形塑法律,[48]培养公共管理者的“行宪能力”(constitutional competence)等,[49]都代表着法律与行政动态整合的可能路径。
不过,新行政法和治理并不是最终答案。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软法虽然体现了统一法律与伦理、立法与政策、裁量与责任的可能性,但也面临着缺少牢固理论基础、危及法律的预测性和简明性、易为权力主体所用等困境;[50]治理也会失败,需要国家承担“多元治理”的角色来为不同层次和不同要素的治理安排提供协调一致的平台;[51]在从管制向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多元利益的相互促进常常只是权力和资源分配中的少数特殊情况,而多数情况是“向另一个主人下的重新管制”。[52]法律与行政的动态整合体现了一种可能甚至已经部分达成的趋势,但如何取得良好效果仍是一个不设答案的开放性议题。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挖掘公共行政的公法传统,本文重述了行政法与行政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的公法模式与管理科学模式之间的关系演变历程:欧洲的行政法传统使早期公共行政内部公法因素与管理因素并存,并在行政国家时代演变为行政法学与公共行政学、公共行政学的公法模式与管理科学模式间的疏离和对立。同时,对管理科学模式的过度强调遮蔽了公共行政的公法渊源并引发了在公共行政中“重新发现法律”的运动,宪法和行政法的实质性变革、司法审查变迁与“新伙伴关系”的形成、新行政法与治理的兴起,导致当代公共行政与法律从分离走向动态整合。在公共行政中重新发现法律的过程,既是公共行政学的公法模式与管理科学模式冲突消解的过程,也是从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观念下的公共行政学向“管理、政治与法律”三维分析路径转变的过程,当代公共行政学的分析维度和理论视野由此得以大幅拓展。
公共行政的管理、政治与法律路径都体现着寻求良好治理的努力,具有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合法性基础,任何单一维度的取向都是对公共行政图景不完整的描绘。法律既设定公共行政的价值目标,又是多元治理工具中的一员,能够提供权威、引导变革,确定责任、协调冲突。在有关公共行政的跨学科研究中,除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资源外,法学尤其是行政法政策学亦可占有一席之地。对行政法治的强调使法律与法治几乎涉及了公共行政的所有领域,现代公共行政在规则制定、政策形成与执行、人事与组织管理等方面都烙下了法律的印记,科学化取向的组织与管理理论要发挥效率也需要合适的法律架构。因而,跳出文本脉络中的既定思维框架,本文对公共行政与法律间关系演进的梳理,也代表着对可能的法政策学或法行政学理论基础的探求。法律与行政的动态整合以及对法政策学或法行政学的探索,不仅能够丰富公共行政的学科理论并为我们观察行政实践提供新的线索,还将为我们理解不同制度语境中的法律体系、政府角色、治理模式乃至政治发展提供一种异于传统认知的新视角和切入点。与此同时,对中国的公共行政学而言,这也将有可能成为对其“身份危机”的一种侧面回应。
当然,法律与公共行政“从分离到整合”并不意味着二者关系的“历史的终结”,无论是治理对公共行政与法律间关系的整合,还是公共行政学的管理、政治与法律三维分析路径,都存在广泛适用与具体讨论的空间。在公共行政中“重新发现法律”之后,围绕着法律与治理的交织、法律与行政的张力以及二者在不同体制下兼容的具体形态和制度安排等议题,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揭示。
[参考文献]
[1][48]Christensen, Robert K., Holly T. Goerdel, & Sean Nicholson-Crotty. Management, Law, and the Pursuit of the Public Good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1, 21(suppl 1): i125-i140.
[2] [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M]. 孙迎春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6-44.
[3]马骏,颜昌武. 西方公共行政学中的争论:行政科学还是政治哲学[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4]Rosenbloom D H. Public Administrative Theor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3.pp219-227.
[5][8]陈新民. 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121-122,135-136.
[6][德]米歇尔·施托莱斯. 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1800-1914)[M]. 雷勇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8-23,510-514.
[7]Wilson W.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887, 2(2): 197-222.
[9]李振,鲁宇. 行政学的威尔逊悖论——学科起源正统史论的袪魅与反思[J]. 中国行政管理,2016(4).
[10][美]弗兰克·J·古德诺. 政治与行政[M]. 王元,杨百朋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44.
[11]Moe R C, Gilmour R S. Rediscovering Principl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Neglected Foundation of Public Law.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5,55(2): 135-146.
[12]Moynihan D P. “Our Usable Past”: A Historical Contextual Approach to Administrative Valu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9, 69(5): 813-822.
[13] [美]赫伯特·西蒙. 管理行为[M]. 杨砾,韩春立,徐立译.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45-47,244.
[14][美] 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 公共行政的精神[M]. 张成福,刘霞,张璋,孟庆存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1.
[15][日]大桥洋一. 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M]. 吕艳滨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62.
[16][19][美]华勒斯坦等.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 刘锋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0,258.
[17]Waldo 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6.
[18]Lynn L E. Restoring the Rule of Law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What Frank Goodnow Got Right and Leonard White did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9, 69(5): 803-813.
[20]Harlow C.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vergence and Symbio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05, 71(2): 279-294.
[21]Dimock M. Lawyers and Managers Look to the Futur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4, 44(6): 461-468.
[22] [美]杰伊·M·莎夫里茨,E·W·拉塞尔,克里斯托弗·P·伯里克. 公共行政导论[M].刘俊生,欧阳帆,金敏正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8-20.
[23]戴维·H·罗森布鲁姆,海伦娜·K·芮妮,叶杰. 认真对待当代公共行政中的行政法[J].中国行政管理,2015(8).
[24][32][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德博拉·戈德曼·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M]. 张成福等校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0,32-42.
[25][美]菲利普·库珀等. 二十一世纪的公共行政:挑战与改革[M]. 王巧玲,李文钊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6.
[26]Lee W Y. Political Scie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Stat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5,55(6): 538-546.
[27][英]马丁·洛克林. 公法与政治理论[M]. 郑戈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45-191.
[28][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 法律与行政(上卷)[M]. 杨伟东,李凌波,石红心,晏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47.
[29]季卫东.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代译序)[A]. 诺内特,塞尔兹尼克. 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C]. 张志铭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6-7.
[30][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斯玛丽·奥利里. 公共管理与法律[M]. 张梦中等译.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32.
[31] [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M]. 毛寿龙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35-156.
[33]石佑启. 论行政法与公共行政关系的演进[J]. 中国法学,2003(3).
[34]Newbold S P. Toward a Constitutional School for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0, 70(4): 538-546; 孙宇.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美国学界的争论[J]. 中国行政管理,2013(11).
[35]Cooper P.J. Conflict or Constructive Tension: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of Judges and Administrato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5,45(5): 643-652.
[36]Rosenbloom D H. Public Administrators and the Judiciary: The "New Partnership".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7,47(1): 75-83.
[37]郑春燕. 行政任务取向的行政法学变革[J]. 法学研究,2012(4).
[38]李洪雷. 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趋势——兼评“新行政法”的兴起[J]. 行政法学研究,2014(1).
[39][新西兰]迈克尔·塔格特. 行政法的范围[M]. 金自宁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前言,2006. 2.
[40]王诗宗. 治理理论与公共行政学范式进步[J]. 中国社会科学,2010(4).
[41][52]奥利·罗贝格. 新新政:当代法律思想中管制的衰落与治理的兴起[A]. 罗豪才,毕洪海.行政法的新视野[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07-279,270.
[42]Bazelon, David L. The Impact of the Courts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diana Law Journal,1976(52): 101-110.
[43]Melnick R S. The Politics of Partnership.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5: 653-660.
[44]Yarbrough, Tinsley E. The Political World of Federal Judges as Manage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5,45(5): 660-666.
[45]O'Leary R, Wise C R. Public Managers, Judges, and Legislators: Redefining the "New Partnership".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1,51(4): 316-327.
[46]Zouridis, Stavros. Rule of Law or Law Overruled? Why the Rule of Law Should Be on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genda. NISPAce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2011, 4(2): 23-37.
[47]刘艺. 封闭与开放:论行政与行政法关系的两重维度[J]. 南京社会科学,2013(5).
[49] [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詹姆斯·D·卡罗尔,乔纳森·D·卡罗尔. 公共管理的法律案例分析[M]. 王丛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50]罗豪才,毕洪海. 软法的挑战[M]. 北京:商务印书馆,卷首语,2011. 10.
[51]郁建兴. 治理与国家建构的张力[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1).
From Separation to Combination: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Yu Jianxing Xiang Miao
[Abstract]Administrative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re two branches of general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Early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y still shows the features of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public law paradigm, while the rise of administrative state requir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 adopt the management science paradigm. There is a high tens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vailing management science paradigm and public law paradigm, showing as the anti-la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anti-adminis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The debate over the natur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or political philosophy, ignores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pproach of law from managerial and political approach. The substantive change of the constitutional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 the transition of judiciary review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partnership”, as well as the rise of new administrative law and governance theory, not only promote the dynamic combination of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but also turn the dichotomy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into the analytical approach of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management, politics and law. Governance theory represents a realizing way and potential vision of combining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but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practical effects still remain to be open and uncertain issues.
[Keywords]dichotomy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ve law, management science paradigm
[Authors]Yu Jianxi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Xiang Miao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