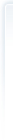
[摘要]省管县体制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视角,对省管县体制改革动因、政府行为差异进行了理论逻辑和现实情境的阐释,并从省管县幅度、行政区划调整、创新主体、核心制度和配套改革等方面提出制度设计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省管县体制改革;成本收益分析;政府行为差异
[中图分类号]D035.5;D63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11)09-0109-05
我国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全国大范围的兴起却在本世纪初。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和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理论探讨和调查分析。学者们总体肯定了省管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和完善举措。二是对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提出了制度构想。从财政省管县走向行政省直管县是多数学者的共同观点。部分学者还对现阶段推行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基础条件、动力及阻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前瞻性建议。尽管国内学者在省管县体制改革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就,但现有研究对政府如何进行制度创新缺少足够的经济理论阐释,在制度设计方面缺乏更进一步的科学严谨论证与分析。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视角来探寻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动因和政府行为差异,为省管县体制改革提供具有理论支撑的推进策略。
一、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省管县体制改革的预期成本
新的制度安排并不能免费获得,需要付出创新成本。预期成本主要包括:一是组织成本。省管县增加了省级的管理幅度和覆盖程度,也增大了县级的工作量和管理难度,可能引起机构和人员的膨胀。鉴于我国各级政府机构庞杂,行政冗员较多,只要省管县数量在一定的管理幅度以内,则不需要大量增设机构和人员;同时由于地级市不再承担管县的职能,还可以减少相应的机构和人员编制。总的来看,省管县后人员可以内部调剂,行政人员总数增加有限。二是联系成本。由于省、县的空间距离远远大于市、县,交通、通信等联系成本可能上升。但一方面,以前县既要联系市,也要联系省,若改革后只联系省,则联系成本不会有大的变动。具体而言靠近省会城市的县域行政联系成本要低于远离省会城市的县域,面积较小的省份行政联系成本低于面积较大的省份。另一方面随着远程数据传递处理技术、先进办公自动化设备和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全球电子政府的快速兴起,政府正从传统的“公文政府”、“纸张政府”向着“网络政府”转变,空间距离的沟通障碍会越来越趋于弱化。三是利益摩擦成本。省管县是省、市、县三级政府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市级政府的人事管理权、财政支配权和行政审批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限制和缩小,市级政府的阻力不小;同时对某些市县而言,本身已经实现较高程度的行政区域经济一体化,一旦在区域上拆散或者打乱,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可能破坏经济一体化进程。但利益摩擦成本在市管县体制中原已存在,来自市级政府的阻力可以通过利益补偿机制来减弱,区域竞争关系可以通过区域合作机制来协调。
(二)省管县体制改革的预期收益
在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制度创新是制度创新主体为获取潜在制度创新收益而进行的新的制度安排,所有的创新主体(个人、团体和政府)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1]按照这种理解,当政府发现省管县能比市管县产生更高的收益时,则会扮演“初级行动团体”的角色,着力推动制度创新。实行省管县的预期收益主要包括:一是县域经济发展收益。由于县级政府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和调控能力,能够针对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及时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优化县域投资环境,县域经济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二是行政管理效率收益。由于减少了行政层级,实现了政府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弱化了信息传递中的失真问题,保证政令畅达,行政管理效率得以提高。
综上可见,省管县的预期收益较高且能确定,而预期成本相对较低并有一定的调节空间,只要省管县的数目适度,则存在着较大的制度创新净收益。相对而言,省域面积越小、县域经济比重越高的省份潜在的制度创新净收益越高,地方政府推动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动力越强劲。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省管县体制改革率先从浙江开始发动,又以浙江最为成功。当然,制度创新收益和成本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可能体现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即使省管县在经济层面出现了净收益,但如果有较高的政治成本和社会摩擦成本,则改革将难以发生。我国西部一些省份由于涉及到敏感的民族问题和边界安全问题,省管县体制改革进展较慢。
二、省管县体制改革的行动主体与行为差异
在目前的省管县体制改革中,政府是最主要的制度创新主体。然而,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省、市、县政府制度创新驱动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制度创新收益,更由于多个利益主体的存在,以及各级政府在制度创新中收益分割和成本分担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从而有着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一)中央政府:静观其变、支持参与
随着省管县体制改革带来的地方经济更快增长,按照中央和地方商定的财税分成种类和比例,中央政府能够更多地参与分享制度创新收益。一般而言,参与改革的省份越多,带来的新增经济总量就越大,中央政府就能分享到更多的制度创新收益。承担较低的制度创新成本却能分享到大量制度创新收益,因此,中央政府对各地有管县体制改革的态度从初期的静观其变转变为明确支持,到后来甚至规定财政省管县的任务时间表,显示中央政府在省管县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依次扮演了制度创新的静观者、支持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二)省级政府:利益驱使、积极推动
对省级政府而言,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收益是实实在在的,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将迅速壮大省域经济实力,税费的增加让政府有更多的财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或者增加行政办公经费和工资福利。但另一方面,省级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直接承担着制度创新成本,管理难度和行政支出成本可能将随辖县数目增多而增加。作为省管县体制改革具体的制度设计者和执行者,不同的改革路径和制度设计影响着省级政府的收益分享和成本分担,作为“经济人”,省级政府总会选择收益最大化的改革方案。由于县域之间经济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和发展潜力又存在很大差异,省对每个县的管理成本虽有差别但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同样实行省管县,强县的制度创新预期净收益明显高于弱县。因此,理性的省级政府在试点时总是从经济强县开始,然后在管理幅度允许的情况下向中等县、贫困县延伸。从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省份在试点时都优先选择经济强县,而经济基础薄弱县则大多被排除在外或被延后,这以浙江最为典型。
浙江从1992年开始对经济强县进行了四轮放权,直到2009年才将放权对象从强县扩至全体县市。其他如湖北、河南、山西、安徽、广东等省均选择经济强县先行试点,其中安徽还对试点县实行动态管理,试点县(市)身份并不固定,它们需要接受每两年一次的考核,达不到考核目标要求的,将予以调整。[2]只有江西采取了弱县扩权先行先试的谨慎政策,先在2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市进行革试点,后来进一步扩大到59个县市。
(三)地级市级政府:坐等观望、被动参与。
地级市政府在省管县体制改革中的处境极为尴尬。如果实行省管县,从理论上可以获取城乡分治后城市专业化管理带来的分工收益,但事实上地级市政府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市区,这方面收益不多。最重要的是,原来截留县(市)各种资源的机会没有了,行政层级上的政治优越感也不复存在,雍肿的机构和人员还得自身消化,甚至一些省在试行“省管县”后仍实行市对县补助不变的政策,让市级成为利益净流出群体。综合权衡来看,地市一级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一方。因此,地级市不可能心甘情愿地积极推动改革,而是想方设法维持旧的格局,坐等观望甚至成为改革的阻力方。最明显的是浙江推行财政省管县后,地市不断游说省级政府,欲将县重新纳入市财政管辖。但是面对着上级政府的改革压力,以及下级政府的改革热情,地级市政府无法进行明目张胆的抗拒。一些地级市政府公开响应改革,其实并非源自于真心实意的拥护,而更多的是无奈之下的被动参与。
(四)县级政府:积极争取、主动参与
若能成为省直管的对象,县级政府是直接受益者。县域资源将不会再被地市所截留,和过去相比就相当于多了一块收益。随着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不仅让政府有了更多的可支配财力,也为政府官员提供了展现政绩的机会。县级官员与地级市官员的关系从上下级转变为平起平坐,政治地位提升带来的愉悦都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县级官员有了更多与省级官员直接沟通的机会。在省管县管理幅度有限的情况下,不是每个县都有机会参与。因此,各县市总是想方设法进入试点县名单。针对省级政府“强县优先”的改革行为,普通县和贫困县极为不满,纷纷要求加入改革试点。于是一些省份采取折衷的妥协方式,在选择强县试点的同时兼顾一般县和贫困县。如安徽首批确定10个强县,后来考虑平衡因素,又补加“毗邻苏浙地区”的广德县和经济欠发达的岳西县。山东则对30个经济强县和30个经济弱县同时实行试点,但采取了有差别的政策:对经济强县给予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分配自主权,对于经济欠发达县则实行扶持政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河北省22个试点县中除16个经济强县外,还包括6个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县。
三、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推进策略
(一)统筹考虑创新成本与创新收益,科学界定省管县的管理幅度
省政府应如何决定省管县数量?改革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制度创新收益,因此,可以合理假定,省政府关心的是改革的收益最大化。由于每个县域并不是均质的,省政府应统筹考虑创新成本与创新收益,应先将制度创新收益高的强县列入省管县,然后按照收益的差别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根据经济学的供需分析模型,只要新增加的一个省直管县所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改革就能增加总收益。当省管县数目的增加不再带来收益的增长时,就达到收益最大化。这时最后新增加的这一县域产生的制度创新收益和增加的制度创新成本相等。理性的省级政府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就不会再扩大省管县数目(图1中MC0为边际成本曲线,MR0为边际收益曲线,Q0为确定的省管县数量)。从动态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管理可能出现以下变化:精简机构和人员,政府改变管理方式,增强县域自治能力等,同时县域经济实力可能普遍有所提升。这会导致边际成本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的移动,省管县数量也会变动(图1中Q1为边际收益不变而边际成本曲线下移至MC1时确定的省管县数量;Q2为边际成本不变而边际收益曲线上升至MR1时确定的省管县数量;Q3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同时变动时确定的省管县数量)。
图1省管县数量模型
注:图中横轴Q为县域数量,纵轴为省管县改革的收益R与成本C,MC为边际成本曲线,MR为边际收益曲线,Q0、Q1、Q2、Q3为确定的省管县数量。
可见,即便是同一省份,其省管县数量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变革和技术的进步而变化。由于各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边际成本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不相同,由此导致各省的省管县数量也不应相同,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全国省管县幅度。在现行省级行政区域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也不宜将所有县域进行省直管。就我国区域经济总体差异而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基础和发展水平要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样推行省管县,则前者产生的制度创新收益高于中西部。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地势较为平坦,省域面积较小,县域与省会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较短,交通通讯也很便利,实施省管县的制度创新成本也低于中西部。因此,总体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省份更有条件实行省管县,其省管县的数目即管理幅度也会大于中西部省份。当然,现实改革比标准分析模型复杂得多,经济因素并非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唯一决定因子。
(二)在现行省级行政区框架内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
我国地域辽阔,如果取消地级市,则平均每个省要管辖81.6个市、县,这显然超过了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针对这一难题,学者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并县论,主张大规模合并县(市)域来减少县(市)域数目,从而在现有省级行政区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省直管县;一种是缩省论,主张划小省区范围增加省区数量。并县论受到缩省论者的猛烈批评,认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行政区划的层级问题,因为县域的倍增,将不可避免的会在大县与乡镇之间出现新的层级,并且会触动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3]目前国内大多学者持缩省论观点。但缩省论真的可行吗?按照缩省论者的主张,要在现有省区数量上再增加约20个省区,这将增加一笔巨大的行政成本支出。可以设想,新增加的省级机关人员可从现有的行政队伍中调剂,人员总量和行政支出可保持不变,但这个假设缺少经验性研究的支持,实践却证明了与之相反的结论。如重庆从四川析出后,两省财政供养人员和行政支出的合计数均大幅增加。可见,大规模地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省级行政区划调整,至少从成本-收益比较而言是有较大经济风险的。
因此,从降低省管县体制改革成本角度出发,大规模并县或大幅度增加省域数量均不可取。比较稳妥的是采取并县与缩省并举的办法,并尽量在现有省区框架内进行改革。这就意味着,对改革的总体目标一定要明确,省管县体制改革虽然是大势所趋,但并不宜将所有的县都列入省直管。中国地域辽阔,从省到县地域千差万别,改革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像上世纪80年代实行市管县那样各地一哄而上。按照这样的理解,每个地区都应出于成本-收益考虑,自主选择适合自身的制度安排。对于经济实力强、城市发展受到空间限制的地级市可将邻县并入;城市化水平高、城镇成片分布的县(市)也可以共同成立新行政区;人口稀少、经济发展条件较差的地区可继续实行市管县。至于省级区划调整,原则上不宜大动,可进行微调。对于所辖市、县超大的个别省区,可以考虑适当划小;对于城市辐射功能强大而辖区偏少的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可以适当扩大其管辖区域,将周边部分县市划入其行政区域。
(三)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和成本分担机制,调动各级政府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各级政府作为利益相对独立的制度创新主体,其对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预期是不一样的。即使从整个国家的角度看省管县体制改革是划算的,但具体到各级政府则有所不同,甚至某级政府出现负收益。这导致不同层级政府在省管县体制改革上存在着制度创新需求和制度创新供给上的差异。为了增加制度的有效供给,需要在各级政府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和成本分担机制,确保制度创新参与各方得到正的净收益,以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
目前中央政府在省管县体制改革过程中基本不付出成本或付出很少的成本,但却通过财政、税收等方式分享了大量的制度创新收益。这种类似“搭便车”的行为由于减少了各省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可能存在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形。为此,建议中央政府在获取的制度创新收益中切出一块回馈改革省份,以增加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率,诱导更多的制度创新发生。同时,中央政府在省管县体制改革中应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主动分担更多的制度创新成本,以调动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
省级政府是省管县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创新主体,由于掌握着省内制度创新收益的分配权,其在改革中的利益能得到保障,积极性不成问题。但如果仅仅保障自身利益而参与改革的县没有相应的利益分成,则改革成效将大打折扣。如浙江早在1983年就开始实行财政省管县,但到1993年全省47个县市仍欠发工资。1994年起省财政推出财政递增综合分成的财政政策,并对不同类型的市、县(市)实行不同的补助和奖励政策,如“亿元县(市)上台阶政策”和“两保两挂”等。实践证明,通过创新收益分享极大地调动了各县(市)的积极性,并激发了县域经济活力。到2003年底,浙江各县市连续11年没有发生拖欠工资的事例,成为全国唯一靠自身财力解决了公职人员、中小学教师工资问题的省份。[4]因此,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成功首先要确保参与县能分享到足够的制度创新收益。
针对地级市难以分享制度创新收益却在承担制度创新成本的状况,可以从增收和减负两方面进行利益调整。一是在制度创新收益中切出一块给地级市,以减少改革阻力,也符合公平性原则。浙江的做法值得借鉴,浙江在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后,从上缴省里的20个百分点中拿出5个百分点来“收买”地级市,以使改革能顺利推进。二是减少地级市的财政支出项目,财权与事权要匹配。由于县级财政收入不再上解到市财政,市对县的配套资金不应再由地市承担,而应进行全省统筹。按权责利相统一原则,对市、县之间的事权也要同步理顺,若需要地级市对县承担部分基本公共服务,则省、县应对地级市进行财政支付作为补偿。此外,若省、县需要增加行政人员,则优先考虑在地级市现有行政人员中调动,以减少地级市的人头费支出。
对于一些暂未纳入省管县试点的县市,应通过省内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让其间接分享改革收益,以减少改革的各种阻力和县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四)及时改革核心制度,突破“制度陷阱”
中国改革历来走的是一条渐进式制度创新之路,其核心思想是先易后难,具体到制度体系是先经济后政治,经济改革又是先增量后存量、先外围后核心。其优点是改革初期遇到的阻力较小,改革容易推进。这种改革思路作为一种经验传承已形成一种路径依赖。省管县也如此,各省在改革初期往往选择在财政体制上单边突破,在财政上进行强县扩权,然后逐步增加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涉及的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原属地级市的经济和财政权,基本不涉及行政、司法、组织人事等事权(有的涉及到人事管理方面),没有正面接触市管县行政体制,容易出现“两个婆婆”的问题,反而增加了交易成本。这种渐进式改革在改革初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可以绕开现行法律、行政等方面的制度约束,也避免了与地级市的正面冲突,大大降低了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但财政省管县到一定程度,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及时跟进。因为在省管县制度体系中,行政省管县是核心制度,而财政管理体制从属于行政管理体制属于一般配套制度。如果核心制度供给短缺,则无论进行多少配套制度的创新,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率不变或者下降,从而跌入“制度陷阱”。像浙江这样的省份,财政省管县的时间相对较长,一般意义上的配套制度已较为完善,单独的财政省管县或一般性的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制度创新收益已接近极致,如果不及时进行行政省管县的体制突破,将难以再产生增量制度创新收益。事实上,浙江地级市的权限早已被虚化,地级市的阻力已经很小,但撤销地级市的决策权在中央而非地方。因此,财政省管县到一定程度,中央政府必须积极参与改革,对具备条件的省份,应允许撤销地级市在行政上实行省县对接,实行完全意义上的省管县体制,以实现尽可能多的制度创新收益。
(五)进行综合配套改革,降低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一是建立高效的制度监督体系和民众参与改革的制度平台。为了降低制度创新风险,不仅要在行政体制内部进行监管,也要发挥体制外社会团体和民众的外部监督作用,建立高效的制度监督体系,避免出现权力一放就乱的状况。实践证明,外部监督不仅富有实效,而且不需要政府承担任何成本。为此,要建立各种制度化的平台设计让民众积极参与省管县体制改革,增强社会监督。
二是权力下放过程中要减少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的过度干预。不仅要将原属地级市的管理权限移至县,还要将省级政府的部分管理权限下放到县,增强县域的自治能力。要借助于权力下放,对各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和审批事项进行大清理,凡市场和社会组织能解决的事项政府不要再插手,将政府的管理职能和管理事项尽量减少,要先清理后下放。
三是成立跨行政区域的协调组织。在规范地方政府职能和行为的同时,可以考虑成立跨区域协调组织,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生态治理等方面自主协商。这种平等、协商的组织可以突破原来地区一级行政区域的界限,为在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可能,而省级相关部门对于跨行政区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可以担当指导和协调的角色。
四是注重分类管理。如按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县域分为发达县、欠发达县和贫困县;按产业差异分为林业县、粮食县、旅游县和工业县等。对县域经济的分类管理一方面能减少省级管理的复杂程度,使省级政府的管理职能从微观转向宏观,有利于增加行政区域管理幅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同类县域之间的公平竞争,激发各类县域的经济发展活力。
五是进行县域政府管理职能再造,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推进积极推进县政建设。要积极转变县级政府的职能,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实现政府的功能性变革,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使政府的结构和职能与县域地理环境、发展条件、经济规模和结构等要求条件相吻合,真正致力于提供一个有效降低交易成本、鼓励竞争和创新的制度环境。[5]同时要合理控制县乡(镇)机构和人员,扩大乡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建立新型的县乡关系,防止以任何藉口擅自提升县乡领导干部的行政级别,避免改革成本的不断攀升。
四、结语
省管县体制改革是对我国新时期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有效模式的制度探索。改革需要理论支撑,有理论基础的改革更具有理性,也更能够深入。[6]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省管县体制改革具有很强的理论阐释力,对于进一步明析改革的方式和路径也很有启发。
第一,潜在制度创新收益的存在是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近年来各省市进行的改革实践,基本上是地方政府为寻求潜在制度创新收益的一种自发行为。中央、省、地市、县作为利益相对独立的创新主体,均会从各自角度对制度创新的收益和成本进行算计,这导致从中央到省、地市和县级政府不同的改革态度和行为。即使省管县体制改革总体上出现了预期创新收益大于预期创新成本这种情形,但因为政府间的利益摩擦和阻滞,也可能存在“制度供给不足”和创新“时滞”的问题。改革是对利益格局的再调整,为形成改革合力,在各级政府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和成本分担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但具体路径和实现方式却可以不同,应在制度“菜单”中选择收益最大化的制度设计。由于不同制度设计的收益和成本不一样,制度设计不应是理想主义者的游戏而应充分考虑经济绩效方面的差异。正因为如此,“强县优先”具有相当的经济合理性。同样,省管县幅度也不能人为先验地确定,其管理幅度应由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来决定,当新增加的省直管县创新收益和创新成本相当时,是省管县最佳数量。
第三,为了保证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成功,精心的制度设计是必要的。单方面的“并县”或“缩省”存在增加改革成本的风险,而“并县”与“缩省”并举,尽量在现行省级行政区框架内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并非是简单的折衷,而是出于降低改革成本的需要。在具体的制度体系设计中,一方面要及时改革最核心的制度——实行行政上的省管县,以避免陷入“制度陷阱”;另一方面要进行相应的综合配套改革,以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美] R.科斯,A.阿尔钦,D.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72.
R.Coase,A.Alchian,D.North et al..Proper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Collected Works of the Property Rights School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chool.Trans.bu Liu Shouying.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91.p272.
[2]谢良兵.省管县:“无为”之治[N].经济观察报,2008-09-01.
Xie Liangbing. Province Administrating County: The Rule of Inaction.Economic Observer, 2008-09-01.
[3]贺曲夫,刘君德.省直辖县(市)体制实现的路径及其影响[J].经济地理,2009(5).
He Qufu, Liu Junde. Analysis on the Realization Route and the Effect of Province Directly Administrating County(City) System. Economic Geography, 2009(5).
[4]吕君,王小聪.从“浙江经验”看财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6).
Lv Jun,Wang Xiaocong. Overview of the Reform of Province Administrating County System through“Zhejiang Experiences”. Journal of the Postgraduate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2006(6).
[5]杨茂林.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推进县政建设——从“省直管县”的视阈谈起[J].中国行政管理,2010(5).
Yang Maolin. Promoting County Administration Based on the Focus of Public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vince Administrating County”.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0(5).
[6]张占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实践创新[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49.
Zhang Zhanbin. Practical Innovations of the“Province Administrating County”Reform.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Press,2009. p49.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福州350001)
Governmental Behavior Difference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Province Administrating Country” Reform
Xiao Qingwen
[Abstract]“Province Administrating County” (sheng-guan-xian) reform is an institutional change process. This paper is designed to logically analyze its underlying forces, the differences of governmental behavior and reform strategi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are thereafter presented, including the scope of this new system, adjust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innovation subjects, key systems and related reforms.
[Key words]province administrating county reform, cost-benefit analysis, difference of governmental behaviors
[Author]Xiao Qingwe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Fuji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CPC. Fuzhou 35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