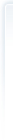
基金项目:民政部委托课题“村落解体现状与乡镇治理的路径选择”(2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乡村治理转型中的农民政治心理嬗变”(编号:10YJC810028);第5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编号:2012M511228)
作者:刘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后,武汉430079
[摘要]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村落社会的快速解体及其对乡镇治理的影响值得我们重视。通过2009年7月和8月针对中国11个省19个村落的调查,可以发现,当前中国广大村落普遍存在解体的趋向,但各地村落解体的层面和程度均存在区别。今后,国家在总体上加大对农村投入的同时,应结合各地不同村落的解体状况采取相应的治理对策。对于那些传统治理资源还比较丰富、共同体保留尚好的村落,国家应保护并利用村落自身的机制来实现治理。对于那些部分解体的村落,国家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以实现村落的长远治理。而对于那些已经基本解体甚至严重萎缩的村落,国家则可以统一规划,加大介入的力度,并试图在新的基础上帮助新型村落建立共同体。
[关键词] 村落解体;乡镇治理;路径选择;重建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063,D0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4)05-0064-06
本文关注的是我国村落在近十余年来普遍走向解体直至凋敝的现实,以及这一现实对我国的乡镇治理带来了哪些挑战。当然,这里所讲的村落主要是自然村意义上的。与行政村不同,自然村更具有与传统村落相关的延续性,自然村落的巨变尤其是其解体直至凋敝,对中国乡村社会本身的影响或许是根本性的,其对中国国家治理尤其是乡镇治理的影响也将是根本性的。
正是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独特传统、经历的独特改造以及农村的尴尬现实,当前在学术界出现了两类互相争论的观点。总结来看,其中一类观点认为,目前农村的尴尬是由中国现代化不足带来的,如城市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水平还不高,只要待以时日,城市化(城镇化)和市场化逐渐深化,问题最终就会解决。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当前农村出现的种种乱象和发展困局,主要是因为现代化过快超越了村落的内在承受力。因此,要反思我们现在主导的快速现代化和强势的国家政权建设,强调将村落社会重新建设成为理想的生活家园。
笔者认为,出于对传统村落的诗意想象和情感留恋,试图阻止整体上村落衰败的趋势,无疑是不现实的。因为村落的命运已经不仅仅取决于自身,更依赖于裹胁着它们不断转型的现代化大潮和外部世界。更为理性的态度可能是,一方面,承认从总体上和最终的大势上,我们难以改变村落衰败直至部分消亡的趋势,换言之,“村落的终结”[1]是我国相当部分乡村或城中村的归宿;但另一方面,从一段时期和某些区域看,村落是否可以在新的条件下焕发活力,以使我们在单向度的现代化面前依然有多样性的生活选择?而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可以采取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的办法介入村落?考虑到我国独特的国情,广袤的村落、庞大的农村人口和有限的耕地,村落短时间内的快速衰败,对我国的现代化可能会带来损害,而我国各地村落的发展也并非完全定型化,因而存在努力的空间。显然,对于我国各地村落发展的实际状况,有必要从村落解体的角度展开调查,并进而确定乡镇治理的有效路径。
一、村落解体的概念与指标
我们这里所讲的“村落解体”,是相对于传统村落的“自成一体”状况而言的。从理想类型上看,传统村落具有自主性,其作为社会基本单位,内部具有紧密的联系,并能很好地通过自身的循环系统满足其需要。具有表现如下:自我提供公共产品,自我生产帮扶体系,自我满足消费欲望,自我维持内部秩序。而从成因上看,以上的诸多特征依赖于相应的内外支持结构:从内部看,村落的自然条件与空间分布,熟人社会的特质,交换圈的客观存在,资源总量限制与模糊化利益,民间信仰体系都是至关重要的变量;从外部看,“编户齐民”的限度,“皇权不下县”与乡绅的非正式治理,政府的重农观念与休生养息的理念,村落与国家共享一套文化符号,是非常关键的外部结构性因素。[2]
系统解析村落自主性的形成机制,可以发现其维持所需要的独特的社会条件,因而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应该说,当前我国的村落,在主要方面不可能完全具备传统村落的以上性质。相反,处在快速现代化语境下的村落,更多的是走向解体的,也即,其内部联系变得越来越松散,其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其靠自身的组织系统解决其问题的能力趋向弱化。这一点,已被众多乡村调查所充分证实。[3][4][5]
换言之,本文对村落解体的判断,主要是其自主性的逐步弱化直至丧失。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测量村落的解体程度,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村落的类型。村落解体的具体测量指标,可以按照如下几个大的方面来设计,综合考虑村落解体的程度进行判断:
其一,常住的人口规模及其结构。一定数量的常住人口是构成社会共同体的前提,因为,只有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他们在合作的基础上才能解决面临的公共问题,他们之间的互动也才能使共同体得到延续;而人口内部的结构同样非常重要,性别结构、老中青幼的年龄结构必须具备一定的均衡,否则其社会关系及其延续性将成为很大的问题。
其二,村民间相容性利益的存量。也就是说,居住在村落中的村民之间具有一些共同利益,有一些事关所有人的事务,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可能因为利益关联而走到一起。一般而言,相容性利益存量越丰富,村民之间的关系就越紧密,他们之间的互动也就越频繁,村民对作为整体的村落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也就越高。相反,如果相容性利益较少甚至稀缺,村民关系就相对松散,他们之间的互动就不那么频繁,他们对村落共同体就会失去关注的热心。
其三,村落公共生活频率与效果。即村落作为一个生产、生活和娱乐空间,是否能够举行经常性的公共活动,让所有村民或大部分村民都参与其中,并能获得一定的收益。这一方面与前面的第二个方面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又存在区别。村落的公共活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超越性。如果村落公共生活的频度比较高,社会效果比较好,本来关联比较弱或意识不到彼此密切关联的村民,也可能因为公共活动而对其他村民表示关注,并对村落的各项事务表示关心。也就是说,公共活动具有延续和建构村落共同体的功能。
其四,村落精英质量与功能发挥。村落无论在什么时期,相对而言,都是国家权力深化比较弱的空间,其至多多少少都具有自然性和自治性。在这样一个比较自然和自治的空间,当地精英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也更为关键。很难想象一个秩序良好的村落没有相应的精英,更难想象精英功能不能很好发挥的村落,其自给自足能够长期延续。
其五,村民间生活交往及其互动。就日常生活的角度而言,村民之间能否互助以克服某些村民面临的难题,对村落共同体而言也非常重要。家庭个体的力量毕竟是弱小的,而乡村生活又面临一些不可预料的因素如自然灾害、疾病或其他变故。在这种情况下,相邻的村民或具有血缘关系的村民能否互相帮扶,是衡量一个村落内部的社会关联是否解体的重要指标。
其六,面向村落的持续发展取向。也就是说,村落中的人是否将主要的关注点和生活归宿放在村落,还是将目光放在村落之外,而普遍希望离开村落到外面发展。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只有大部分村民都把村落当成自己最重要的家和安身立命的所在,村落才具有了长期延续的可能。否则,村落就变成开放性的,它的价值和地位就趋于下降。集中体现就是他对年轻后辈失去吸引力。
二、村落解体的现状
为大致了解当前我国各地村落的解体现状,本研究于2009年7月和8月进行了规模适中的实地调研。部分调研由笔者亲自完成,部分调研由经过笔者培训的乡村调研员完成。我们共调研了11个省的19个村落。这些村落中,既有发展态势比较好的、一般的,也有发展态势比较差的;既有城郊村、一般位置的村落,也有比较边远和落后的村落;既有少数民族居住的村落,也有一般性的村落。应该说,村落的类型还是比较全面的,对了解我国村落的解体现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具体调查中,我们主要分三块:第一块是对村民进行村内关系和乡镇建设方面的问卷调查;第二块是对乡镇干部进行乡镇建设和村落发展情况的深度访谈;第三块是在有调研条件的村落,深度跟踪村落中近期发生的各类群体性活动,以此具体呈现和判断村落解体的状况。
这样,我们主要取得如下三个方面的初步材料:其一,444份调查问卷,问卷中既有客观题,也有主观题目;其二,乡镇干部的访谈记录;其三,关于村落发展和村民群体性活动的说明性材料。
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材料,结合前述测量村落解体的一系列指标,我们发现,当前我国村落在总体上是存在解体的情况,并有进一步解体的趋向;但不同地区的不同村落之间,又在解体的方面和解体程度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别。
(一)常住的人口规模及其结构。调查发现,现在大部分自然村落中的常住人口比十年前都有大规模减少,一方面是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至多在农忙时或过春节时才大规模返回家乡;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外地定居,包括乡镇、县城或打工地居住,他们甚至有不少选择举家搬迁,他们的小孩也有很大一部分在入学年龄后就离开家乡。人口规模的减少在部分村落达到全村人口的60%-70%,一般也都在40%以上。个别严重的如陕西某村甚至只有7个老人。人口规模的急剧缩减,使得村落很难展开经常性的群体性活动,也很难展开有效合作。因为他们加在一起的力量也很弱小。剩下留在村落的主要是老年人、中年以上的妇女和部分小孩。老年人或许不愿或者不能离开故土,妇女往往是因为要照顾老人和小孩,她们同时要承担繁重的田间劳作,而小孩的数量同样也急剧减少。我们看到,不少村落的小学因为生源渐少而难以为继,只好走倒闭或合并的道路,而乡间小孩的玩伴也多成为遥远的梦想了。常住人口的结构出现很大危机,他们的素质同样令人担忧,这使村落自身的循环系统紊乱。
(二)村民间相容性利益的存量。当我们向普通村民、村干部和乡镇干部询问村落集体利益时,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村里集体资产比较薄弱甚至没有。不仅是行政村意义上的集体资产现在大都不多,自然村意义上的村落共同财产更是所剩无几。乡镇干部和村委会的干部一般都向我们表示,村里要想办点事或推动一些自然村落办一些事,行政村里没有一定的财力是很难想象的。而在我们这次调查的村落中,除了福建某村因为集体林权一直没有分配给普通村民,村集体通过比较好的经营不仅保证了村民的收益,也保障了村集体的财政基础,从而使村集体有财力主办了不少公益事业和公共工程,其他的村落基本上都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村集体不再掌握丰厚的集体资源。应该说,村民之间,尤其是自然村落范围内,村民事实上还是存在一定的相容性利益,如水利和道路。但在这些问题上,村民之间过于计较得失,较少能够一起合作完成。反而是在某些具有民间信仰意味的活动上,如云南某村及陕西某村,他们表现出难得的一致性。这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
(三)村落公共生活频率与效果。根据调查,我们发现,村落中的公共生活,包括宽泛意义上的各类群体性活动,其展开的频率都大不如以前。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3的村民认为村里出现大事后,大家并没有聚集在一起讨论。除了行政村意义上的选举之外,自然村落意义上的村民小组组长选举,小组会议的开展并不多。真正比较多见的,主要是婚丧嫁娶和民间信仰等文化活动,只有在这些活动方面,村民才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其他的活动,真正关系到村民利益和发展的活动,如公共工程和经济合作,都很难展开。有的地方甚至是“成片成片的田地都被抛荒了,人们渐渐发现与其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不如出去打点零工赚点钱来的实在。关于修复渠道也渐渐无人问津了。”(2009年7月调查笔记,编号:20090701)公共活动开展的效果,除部分让村民比较满意外,大部分他们都评价不高,尤其是对选举和民主方面,他们一般都表示出不满意,认为存在拉票、派系和“不平等性”。相当多的公共活动如土地分配和选举展开后,村民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加恶化,他们不仅不信任精英,也不相信彼此。相关的主观回答和文字材料也都能显示出这一点。
(四)村落精英质量与功能发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从乡镇干部到普通村民,他们都普遍表示出对现有村落精英水平和能力的不满意,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也显示,超过1/3的村民认为他们的发展“缺少带头人”,而对村落出人才或吸引人才的前景更为担忧。他们从心底期待有优秀的带头人,但他们又觉得真正的人才很难走进乡村。有的村落,年轻人不愿担任村里的领导人,村里领导班子年龄普遍在55岁以上。部分村干部只想着自身的利益,完全不顾村民的利益。现有的村组干部一般都难以取得村民们的普遍认同,村落精英的外流严重,余下的村落精英也并不将主要心思放在本村的发展上,他们要么埋怨村干部的待遇太低,要么埋怨村的工作不好做,所以他们虽然在其位,却热衷于其他生存和赚钱的途径。村落精英的功能发挥虽然在形式上还得到一定的延续,如村落精英参与婚丧嫁娶和民间信仰的组织活动,但他们在解决纠纷和带领村民发展方面,往往无能为力。因为,现在的村民越来越独立,越来越个体化,他们并不轻易承认村落精英的权威。
(五)村民间生活交往及其互动。与传统的村落,尤其是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村落相比,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就是,村民之间普遍的往来减少了。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村落中“人心涣散”。现在村落中真正往来比较多的,一般都是亲缘关系非常近的几个家庭之间。村内一般村民之间的互助有减少的趋势。当然,一小部分的村落,村民之间还是能够保持比较频繁的交往和互动的;但大部分村落,村民们聚集在一起单纯的聊天和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了。农活忙完,回到自己家里,门一关,自己家看自己家的电视。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3的村民“不经常串门”了。倒也有一些小规模的村民互动,那就是打麻将和赌博。村民们普遍感觉,现在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前有人情味,因为现在什么都讲钱,只要掏钱,就有人帮忙,不掏钱就很难指望一般的村民了。血缘关系虽然在维持村落秩序方面仍有作用,但利益正越来越成为决定村民关系的最大砝码。在大部分村落,恐怕利益作为影响村民关系的因素已远甚于传统因素。村落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色彩在人与人关系的疏远和理性化中趋于淡化。部分调查员的感慨也很容易得到共鸣:“今时不同往日,农忙时节农民们再也不会相互帮忙了,再也没有以前那种热闹壮观的场面,只是偶尔几家关系十分亲密的人之间才会相互帮忙。现在流行的是自家种自己的地,自家管自家的农忙,忙不过来了就花钱请几个小工,或者找匹马来驮东西。”(2009年8月调查笔记,编号:20090805)就村落秩序而言,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有近一半的村民觉得,村里出现纠纷没有相应的有头有脸的人出面调解。而湖北某村本来出现了小偷,个别村民都已经看到了,村民们却都选择了明哲保身。
(六)面向村落的持续发展取向。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村落精英,还是一般的村民,他们并不满足于村落内的发展,只要有能力,他们都会想法设法地向外发展,开拓其他的发展途径。村落本身的资源有限,发展空间也有限,村落很难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中保持其稳定的吸引力。同时,村落当前的发展态势有好有坏,但在我们问及现有的常住村民他们是否愿意继续在本村发展时,他们大都表示出愿意,这其中很多或许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或已经习惯了乡村的生活。而在我们问及他们是否愿意自己的子女在农村发展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例外的回答“不愿意”。这部分说明他们对本村前途的评估。在他们的价值判断中,外面的世界,乡镇和县城,直至大城市的生活要优于乡村的生活,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继续留在农村。由此可见,村落中的人面向村落的持续发展取向同样有淡化的趋势。
需要强调的是,上面所有这些概括是我们这次调查得到的总体情况。相关材料可以证明,当前我国村落已经部分解体且正趋向进一步解体。但进一步的分析仍是必要的。我们应该看到,大部分村落的解体并非全方位的,相反,村落的解体也是局部性的。前述测量解体的几个方面,并不是说所有村落都同时存在。部分村落存在解体的方面比较少,其解体的程度比较弱,这一类村落可以称为基本稳定的村落;部分村落存在解体的方面比较多,其解体的程度比较强,这一类村落可以称为基本解体的村落;更多的村落是在某些方面出现危机,但在另一些方面还能延续,这一类村落最多,可以称为部分解体的村落。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基本解体的村落,人口稀少,共同利益缺失,缺少公共生活和精英,村民间互动很少,村落的前途非常暗淡。那些基本稳定的村落,人口较多且比较稳定,村民能意识到存在一定的村落共同利益,能够开展一些公共活动,并不缺乏相应的精英,村民间的互动尚可,村落的发展在近期内还比较乐观。大部分的村落是处在这两者之间的,属于部分解体的村落,它们或许有一定的人口和共同利益,但公共活动难以展开或缺乏相应的带头人,或者人口规模不大但能有比较好的互动,但村落前景仍不被看好。所以,需要我们结合具体的村落来具体分析。正是因为不同村落其解体的方面和程度不同,它们对国家治理的意义也就不同。而且这种状况和局面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会延续;同时,通过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努力,部分村落的改观和村落某些方面的改观都将是可能的。
三、村落解体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宏观的角度
从大的方面,放到国家治理的视角下来分析,首先是要看到村落解体的现状对国家当下的治理和长远的转型意味着什么。如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可能值得深思:
(一)对国家治理资源的需求扩大,国家对农村的投入还要加大。总体上看,我国的村落已经普遍地局部性解体,部分村落的解体甚至非常严重。在此情况下,单纯地依靠村落自身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这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各项事业的投入力度,以帮助村落克服其面临的治理危机。可以想见的是,与以前的村落相比,当前及我国今后的村落,其解体程度都是比较严重的,它们对国家治理资源的需求将是异常巨大的,很多村落对国家的依赖性也将增强。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治理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强调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农村建设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更是应予以长期坚持的。
(二)使国家的治理成本急剧加大,短期的治理效果可能不理想。村落解体就意味着国家的治理政策和治理资源的供给缺乏来自村落的有力配合,既缺乏来自村落的参与和表达,又缺乏来自村落的有效制约,国家治理的成效往往大打折扣。例如,湖北某村本来赶上了修路的机遇,因为“村村通”工程是市财政补贴加农民自己出资,但很多农民不愿意出资修建公路,这样就使很多村人心不齐,公路修建不了了之。山西某些村的情况同样如此,一位副镇长的话多少有些无奈:“说你看修路钱也不能国家全掏吧,一般资金是政府出一些,村民再自筹一些,这应该是合情合理吧。但是就有一些村民不交钱,不交钱路也没法修,所以他家门前的路也就空那里了。”(2009年7月访谈笔记,编号:20090715)
(三)影响基层和地方政权的运作,尤其是地方和基层政权的行为模式。村落解体容易给地方和基层政权一个信号,那就是只有统一规划加大介入力度,村落才能实现改观。但这种基于政府本位的思考可能使治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各地村落的解体原因和解体程度并不相同,简单的一元化政策可能只会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四)村落解体程度不同,其治理后果也就不同。这一点与前面所讲到的紧密关联。如前所论,从村落解体的角度,可以将村落从大类上划分为基本稳定的村落、部分解体的村落和基本解体的村落。很显然,解体状况不同的村落,它们对国家治理的需求和影响也将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程度将取决于村落解体的程度。村落解体程度越高,对国家的依赖越强,对国家的需求越大,同时也将影响到国家治理的效果;相反,村落解体程度越低,其自身的治理能力将越强,也会为国家的治理打下基础。
四、村落解体与乡镇治理的路径选择
从国家长远治理的角度看,我们要面对并认真对待当前我国村落解体的现实。一方面,我们承认村落的普遍解体是难以避免的历史趋势,原初的乡土社会终究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我国村落问题的特殊性和各地村落解体程度的不同,对不同的村落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因为,村落的转型在我国要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时期,国家和社会通过能动性可以在部分领域适当介入,以部分扭转过快的村落解体对乡村治理基础的破坏,特别是可以帮助部分有条件的村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共同体。基于我们这次对村落解体现状的初步调查,本研究对国家以后的乡镇治理思路主要提出如下期待:
(一)尊重村落的自生秩序,廓清各地村落的具体情况
主要是传统的和自发形成的治理资源,尤其是文化性的治理资源,特别需要得到保护和尊重。相关研究就证明,如果乡村社会存在一定的熟人连带关系,且这种连带关系能够将基层和地方政权的领导人包容进去,那么这种连带关系将有利于本地公共产品的供给。[6]在这方面,就应该避免过于仓促的整一规划、强行压制或人为建设。而对村落中自发产生的文化性的群体性活动,乡镇应该充分尊重村落的自主性,只是在外围保障村落自发的各种活动不逾越法律的轨道即可。否则,仓促的干预,只会破坏村落中本来就弥足珍贵的自组织能力,同时也会加大村落与乡村政权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在尊重村落文化习惯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引导如文化旅游开发的方式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一方面延续文化习惯对村落的治理功能,另一方面又使文化设施、相关符号及活动成为生产力,在现代市场社会中散发光芒,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直至当地社会的发展。
(二)从总体上加大对村落治理资源的投入,履行现代国家的职责
这主要包括村民作为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如公共交通、政治权利和享受医疗保障的权利。对于近期并无搬迁预期的村落,国家和乡镇都应该尽力帮助它们通路、通电、通水,同时落实合作医疗和其他的社会保障。同时,对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权在落实中央相关政策方面实施严格监督。而对那些地处偏远、非常落后的传统村落,村民对资金和项目的期望异常强烈,因为他们将长期生活于所在的村落,对这样的村落保持比较好而居住人口还比较多的地方,更应作适当的项目倾斜。
这里主要是考虑到,一方面,当前的村落大都面临着精英、资源和人才等方面的内在局限;另一方面,虽然说村落依然保留着各种形式的自生秩序,但这些自生秩序更多的是零碎的、不系统的,彼此之间也不是有机联系的,尤其是不能发挥村落公共事务中积极的治理功能,反而有可能成为消极的治理力量——既消解了现代国家的公共规则也不能实现普通村民的利益。而且,越是从总体上看,越是接近于村落公共事务的领域,就越是如此。[7]因此,有必要加强国家权威在乡镇治理中的作用,同时提升乡镇治理在政府制度化方面的水平。[8]除此之外,在精英大量流出村落的情况下,国家推动重新输入村落以其需求的精英也是非常必要的。当前正在尝试的大学生村官的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最重要的是,使大学生村官真正立足乡村,为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三)针对村落解体的不同状况,尝试帮助村落建立不同的共同体
一方面,因为国家权力在事实上占据着村落发展的各种核心资源,致使村落自身的部分组织和活动一直缺少成长的机会与可能。尤其是在涉及村落公共事务方面,村落自身一直难以作为相对自主的共同体得到成长,而这一点对村落的长远治理来说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另一方面,处在解体状态的村落,客观上需要有一个中间环节来实现村民与国家之间的对接。对村落来说,这一中间环节就是新型的村落共同体。而现有的乡村政权并不能有效地充当这一角色。因此,国家应该供给或让渡出部分资源于村落,使村落基于新的利益基础重新整合与凝聚,而国家权力作为一种外在的监管力量和服务力量引导村落在自我重塑中的各种努力。从而使村落能够在国家的帮助下获得发展,实现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成长。
具体地讲,首先是通过精英的衔接;其次是调整村落所面对的公共利益结构,促进发展型利益和分配型利益的增长,特别是分配型利益的增长;并在前两个进程的同时,着力通过富有成效的群体性活动培育村民对他人(特别是精英)尤其是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改变目前诸多地区村民无法信任精英,也无法信任地方和基层政府而使既有的国家与村落之间鸿沟越拉越大的状况。
同时,由于我国农村的发展严重不均衡,村落解体的程度及其可能转型的空间存在较大区别。因此,应结合各地不同村落的解体现状采取相应的具体对策。对于那些传统治理资源还比较丰富,共同体保留尚好的村落,国家应充分保护并利用村落自身的机制来实现治理。对于那些部分解体的村落,国家可以通过前述所讲的适当方式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以实现村落的长远治理。而对于那些已经基本解体甚至严重萎缩的村落,国家则可以统一规划,加大介入的力度,并试图在新的基础上帮助新型村落建立共同体。小村变大村,条件差的村移民搬至条件好的村,这样有利于整体规划,资金不重复投资,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国家尤其是乡镇政权,在帮助村落建立共同体的问题上,首先应遵循与村民协商的原则
在我们的调查数据中,当我们问及村民希望乡镇以什么样的方式帮助村民发展时,近50%的村民选择的是“与村民协商”,这充分说明村民自身的主体性已经有充分的觉醒;当然,有近40%的村民支持政府统一规划;超过10%的村民选择了“放手让村民自己发展”。这些情况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单纯强调乡镇政权规划和介入的思路应该得到改变。这里的深层原因在于,国家权力在当前村落中依然保持着相对主导却又比较遥远的优势地位,在资源、精英和权力等方面占据着主要空间,但村民对现有国家尤其是基层政权的态度存在矛盾。一方面,村民不得不依赖于国家权力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对国家的相关精英尤其是乡村精英表示出相当的不信任。[9]这说明,国家权力应当转变对村落的介入方式,以一种更能让村民接受和信任的方式进入村落,或者首先要解决其自身的公信力和权威问题,在此基础上帮助村落发展,实现村落治理的转型。
五、结语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依然庞大的农村人口和广阔的农村地区,客观上让我们对单线和一元的发展模式保持应有的审慎与反思。村落在各地的自主性并不均衡,村落的多样性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社会事实,而且并不必然是消极的社会现实。因此,在总体趋向上日渐解体的村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必然意味其不能在新的条件下走向新型的聚合。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帮助部分村落重建共同体,将村落内部的力量整合起来,同时供给现代国家的治理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管理方法和规则),并在现代国家的框架下调整、引导村落的自生性力量。从而真正实现多元村落与现代国家的一体化,也实现在此新的结构关系的基础上村落转型与国家治理的有机统一。这一点,正是我国乡村社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决定着今后我国国家政权建设的质量和后劲。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Li Peilin. The End of Village——A Story of Yangcheng Village.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4.
[2]刘伟.论村落自主性的形成机制与演变逻辑[J].复旦学报,2009(3).
Liu Wei. The Formational Mechanisms and Evaluative Logic of Village Independence. Fudan Journal, 2009(3).
[3]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He Xuefeng. New Agrestic Society: Survey Notes on Village Society in Transitional Period.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3.
[4]梁鸿.中国在梁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Liang Hong. Liang Village in China. Nanjing: Jiangsu People Press, 2010.
[5]陆益龙.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Lu Yilong. Peasant China——Post Agrestic Society and New Village Construction.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6]Lily L. 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7]刘伟.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对村民群体性活动的中观透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02.
Liu Wei. Village Politics Difficult to Output——A Middle Range Study on Villagers’ Group Activities.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9. p302.
[8]赵树凯.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00.
Zhao Shukai. I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Governance of Towns and Village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0. p300.
[9]刘伟.群体性活动视角下的村民信任结构研究——基于问卷的统计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9(4).
Liu Wei. A Study on Villager’s Trust Structure from the View of Group Activities——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China Rural Survey, 2009(4).
Villages’ Disintegration and the Path of Chinas Township and Village Governance
Liu Wei
[Abstract] As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rapid disintegration of rural society and its impact on governance should be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In July and August, 2009, we investigate 19 villages in 11 provinces, and we found that the majority of villages in China have a trend of disintegration, but the level and degree of village disintegration are different. In the future, state in general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ural areas, at the same time,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as for different level of villages’ disintegration. For those which still relatively have rich traditional resources of governance and the communities are still reserved, the state should protect and use their mechanisms to achieve villages’ good governance. For those villages which have partly disintegrated, the state may take an appropriate way to help them to rebuild community in order to achieve long-term governance. For those which have basically disintegrated, state may take a unified plan and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intervention, and try to help them to build village community on a new basis.
[Key words]villages’ disintegration, township governance, path selection,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Author]Liu We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and also Postdoctoral at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