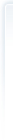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与管理机制研究”(编号:05JZDH0019);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作者:周志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教授;徐艳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1
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5.06.25
[摘要]政府绩效评估一直为信息失真所困扰,博弈行为则是信息失真的重要原因,博弈行为的防治之道相应成为国际相关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本文系统梳理相关理论成果和国际经验,旨在为我国提供启示和借鉴。具体内容包括社会规范建设、提高评估体系的认同度、优化绩效指标体系、改善激励机制、强化监督力度。
[关键词]绩效评估;信息失真;博弈行为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6-0140-06
信息失真是绩效评估中的普遍现象,人为弄虚作假则是导致信息失真的重要原因,博弈行为相应成为国际绩效评估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我们曾撰文对博弈行为的类型及其致因的国际研究文献做了综述和简要评价。[1] 作为后续研究,本文围绕博弈行为防范这一主题,讨论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和国际实践经验。
逻辑上看,防治之道应基于博弈致因的研究成果,达到致因分析与实践对策间的有机衔接。然而,博弈及其致因的系统研究还比较薄弱,难以满足这一要求。第一,由于系统数据的匮乏,绩效评估中博弈行为的研究基本上基于趣闻轶事性质的新闻披露,难以据此对其普遍性和严重程度做出系统准确的判断。第二,现有博弈致因研究或者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主观判断,或者基于小规模心理实验,基于系统数据的实证研究成果为数极少。因此,虽然形成了一些有启示意义的分析框架和结论,但尚未形成普遍共识。第三,为数极少的量化实证研究虽然能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但都聚焦于某一狭小的主题和领域,难以覆盖导致博弈行为的所有因素,也无法覆盖防治博弈行为的多样化实践。鉴于此,本文基于现有文献把博弈行为的防范之道归纳为五个方面,围绕这五个方面对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讨论。
一、社会规范建设:创造诚实守信大环境
在绩效评估中博弈行为致因的多数研究文献中,社会规范被认定为首要因素。Fisher和Downes依据“情境-机制-效果”博弈致因分析框架,通过两轮调研总结出四个影响最大的“情境因素”,要求被访者对其相对重要性赋值(总分10分,分配在4个因素上)。结果是“组织非正式文化对作弊的态度”得分4.5,超过了“作弊被发现的概率”和“受惩罚的严厉程度”两个因素之和(分别为1.4和1.5)。[2] Goldsen 等人对大学生考试作弊的调查发现,虽然81%的被调查者认为作弊是不道德不应该的,但80%的人同时表示,如果其他人在作弊,自己作弊也是可以接受的。[3] Martin做了“宗教虔诚度”(religiosity)与考试作弊行为关系的心理实验,试图验证“宗教虔诚度高的人是否出于内在信念会耻于作弊”这一假设。结果表明,作弊行为受内在信念约束,更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如果看到周围同事在作弊,行动者作弊的概率较高;即使在独处因而没有看到同事作弊的情况下,如果行动者“以为”大家会作弊,他作弊的概率也会比较高;人的作弊倾向与宗教虔诚度不相关。[4] 用Longenecker等人的话说,当某种不良行为日益普遍的时候,它会被社会视为一种常态,“个人就有可能摈弃自己的价值和信念遵从这一‘规范’”。[5]
社会规范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凌文栓等人把诸多社会规范变量聚为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法律规章、社会习俗4个维度,前面两个属于“内控规范”,后面两个则属于“外控规范”。[6] Reno等人把社会规范划分为两种主要类型:“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指大多数人在一定情境中认为有效、正确从而自发形成的规范,如消费中的从众现象;“命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s)指社会、组织、制度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它们通过社会奖惩来驱使个人行为。[7] 作为博弈行为的首要致因,本文中的社会规范有其特定内涵:第一,不包括法律、正式规则等强制性规范,主要指人们自发形成的行为准则,其指导和约束不需要外部强制;第二,不包括信念、价值观、道德观等高层次且内在化了的规范,主要指人们做出的正当有效与否,可取或被社会接受程度的判断,这种判断引导人们的行为。一句话,这里的社会规范指人们基于情境认知而做出的正当性、可取性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自发形成的行为准则。这种狭义界定的社会规范接近于Reno等人所说的“描述性规范”。
上述界定赋予了情境或大环境在社会规范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因为环境作用于人并形塑着人们关于正当性和可取性的判断。这点已为许多跨学科研究所证明。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或“破窗效应”,强调非正常行为与特定诱导性环境之间的关联性。这一理论基于以下观察: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没有被及时修复,那么更多的玻璃会很快被打烂,整个建筑会在大家麻木不仁的氛围中陷入混乱和无序。他们的解释是:环境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会传递一种信息,其他人会受某种暗示性的纵容,从而导致这种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8] 另外一个相关研究是心理学中的自我控制能力(self-control)或自制力(willpower)的自我损耗理论(Ego depletion)。根据这一理论,个体的自我控制行为需要消耗自身的自我控制资源, 而短期内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是有限的;所有形式的自我控制行为使用的是相同的自我控制资源,即使前后具体任务分属于不同领域;自我控制资源会随着消费出现“疲劳”或耗减,个体先前的自我控制行为会造成随后的自我控制行为水平的下降。[9] 比如,第一次观察到大家在作弊能坚持诚实无欺,第二次就不一定能做到,第三次几乎肯定会随波逐流。
综上所述,作为博弈行为影响因素的社会规范是人们基于环境感知形成的态度或非正式文化,它可以冲破内在信念、价值观和道德观带来的自我约束,导致不当行为。当绩效评估中的弄虚作假形成某种气候的时候,组织成员就会随波逐流,心安理得地弄虚作假。这一结论并非用环境决定论为弄虚作假者开脱个人责任,而是强调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对于影响深远的“小过错”,小题大做是非常必要的,以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古语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它最初针对个人的修身养性,对组织治理和防范博弈行为而言,这一箴言同样适用。
二、提高绩效评估体系的认同度
这里的认同度指被评估单位及其成员对现有评估体系的赞同、认可或接受程度。它与博弈行为的关系是:如果被评估单位及其成员对绩效评估体系的认同度低,博弈就会被视为对“不当”考评体系的“合理抵制”,弄虚作假发生的概率就比较高。
依据Fisher和Downes的研究,我们把评估体系认同度归结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绩效评估的组织“嵌入度”(Embeddedness)。绩效评估深度融入组织日常管理,在确认重点工作、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且评估的制度化规范程度高,这种高嵌入度会触发作弊动机。第二,被评估单位及其成员对评估功能定位的看法。如果他们认为评估属外部强加,服务于上级控制目标而对社会公众和组织内部管理水平提升没有实质意义,作弊倾向就比较高。第三,对评估诸技术方面的接受程度。如果他们认为指标体系缺乏多维度的合理平衡,或偏离工作重点导致扭曲,或对指标体系缺乏信任(效度不高、分类不当或时效性差等),这种反感会导致作弊行为。[10]
绩效评估的组织嵌入度与博弈行为的相关性意味着一个尴尬的悖论:降低组织嵌入度有利于防范博弈行为,但这同时意味着弱化评估结果在重点工作确认、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从而降低绩效评估本身的效用。如何掌握绩效评估的组织嵌入度,现有研究成果尚未提出明确的对策和可操作性建议。
针对绩效评估功能定位导致的反感和博弈行为,学术界强调要摆脱目标管理具有的外部强加和自上而下集权特征。Armstrong讨论了绩效管理与传统目标管理的七个重要区别,其中与这里讨论的主题相关的有几点:突出绩效管理诸环节中的雇员参与,强调雇员与管理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协商和相互学习;绩效目标确定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命令和强加过程,而是上下级平等对话、协商和讨价还价的过程;绩效管理是一种共识基础上的契约式管理,强调绩效协议对上下级、管理者和雇员的双向约束,上级不能随意干预或加码;绩效管理是发展导向的管理,突出“人本主义”的管理哲学,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注重雇员个人职业发展和知识、素质、能力的提高。[11]
上述原则在发达国家绩效管理实践中有多样化体现形式。就外部强加集权特征而言,传统目标管理多由人事部门或专门设立的机构主导,而现代绩效管理中则突出直线主管的主导作用,旨在体现绩效管理是日常管理活动一个的组成部分,而非其他部门强加给管理者的额外工作或额外负担。为了减少员工对外部强加的绩效评估的反感,一些公共部门尝试外部政治需求与内部管理需求以及专家职业需求的有机结合,把政治家提出的以财务指标为主的粗放指标体系调整为反映多方需求的精致体系,从而有效降低了博弈行为。[12] 再以共识基础上的契约式管理为例,绩效协议在新西兰被称之为“购买协议”(purchase agreement),即上级从下级“购买”产出和结果,旨在突出绩效协议是买卖双方平等协商的产物,突出上级(买方)对下级(卖方)的承诺,内容包括预算、其他资源保障和权力授予等。美国弗吉尼亚州职能部门的绩效协议中,都包含有州长对局长承诺的内容,体现了契约的双向约束原则。发展导向管理原则在实践中也有多样化体现方式,诸如强化雇员职业生涯发展规划,跨现有岗位的能力培训,结构化的“教练”和“导师”安排等。“教练”重点负责对年轻雇员的业务指导,“导师”则超越业务进行全方位的职业发展指导。[13]
对评估技术方面的认可度主要涉及绩效指标体系改进的问题,这点下面专门讨论。
三、绩效指标体系的动态调整与改进
指标体系是绩效评估信息收集的依据,是管理理念、优先项选择等的具体反映,在绩效评估中发挥指挥棒的作用。指标体系缺陷会引起被评估者的反感从而导致博弈行为,不当绩效指标则会诱发博弈动机并为弄虚作假留下空间。因此,优化和完善指标体系是防范博弈的重要着力方向,有关努力可以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在绩效目标的“挑战性”和“可行性”之间保持合理平衡。这其实是目标管理中一直强调的原则,不过在新环境下有新的表现形式。在德克萨斯州476个学区考试作弊致因的研究中,Bohte和Meier确认了“最有可能作弊”的4类组织,其中包括“资源不足的组织”和“任务难度高的组织”。[14] 考虑资源约束和任务难度密切相关,我们把两者整合为“任务难度”,一个由任务复杂程度、基础、资源和能力匹配度等构成的综合指数。任务难度与博弈行为的因果关系是:政治家满足于确认问题而把解决的任务交给公务员,公民往往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部门面临严重资源约束但又要和其他组织按照同一标准竞争,他们就可能用作弊来实现竞争的“公平性”。
在发达国家政府绩效管理中,在共识为基础的契约式管理理念指导下,上级设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层层下压、层层加码的现象比较少见,目标挑战性与可行性的合理平衡主要表现在: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力度,保障经济落后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需求,提高绩效竞争的公平性;考虑被评估单位履职条件上的差异,避免简单化的横向对比;关注绩效水平的纵向比较,以体现绩效管理追求的持续性改进。
其次,坚持“结果导向”的理念,用“结果指标”取代“产出取向”的指标。结果导向的含义是关注使命和组织目标的实现,指标设计应着眼于终极产品和实际社会效果。[15] 所以,绩效管理在发达国家亦被称为“结果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产出取向指标被视为博弈行为的重要致因:“用量化产出指标衡量部门绩效时,官僚就具有产出最大化的内在动机,不管最大化产出能否带来所期望的社会效果”。这不仅会导致 “目标置换”、“制造工作”无事忙等现象,而且“强烈的产出最大化动机会导致组织作弊,即公共部门有意操纵产出水平为自己贴金”。[16] 这方面一个经典例子发生于美国林肯电器公司,管理层用键盘敲击数对秘书进行绩效考核,结果发现一个秘书利用午休时间敲击同一键钮整整一个小时![17]
这里以交通安全为例讨论产出指标的局限性和结果指标设计。交警的“产出”包括安装的摄像头数、贴罚单数、处理的交通事故数、查处的违规事件数、罚款数额、行政拘留人数等,但产出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交通秩序和安全。如果缴纳超载罚款后可以继续行驶,甚至有“罚款月票”的“便民措施”,产出的提高会带来更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产出指标导致博弈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此类指标具有数目大、主要依靠内部记录和外部难以核实等特点,这些为数据“注水”留下了余地,因而被称为可操纵指标。结果指标的设计其实并不难,交警的使命是维护交通秩序和安全,而作为客观社会效果的安全只能表现为发生的交通事故少、因事故死伤的人少、因事故损失的财产少等。发达国家交通安全管理部门的绩效考核主要围绕这些设计指标。
第三,坚持公民为本理念,用客观指标“中和”过度依赖客观指标可能的副作用。主观指标既包括上级对行动者绩效的评价,也包括服务对象对绩效的评价。这里主要讨论公民满意度为代表的主观指标。从发达国家政府部门年度绩效计划看,95%以上绩效目标属于客观指标,绩效报告中的目标实现状况展示相应以客观指标为主。公民满意度由第三方独立实施,结果独立公布作为参考,不计入部门绩效总分或作为绩效档次划分的主要依据。第三方独立实施和参考定位有助于满意度数据的真实性,这些数据与客观指标数据相互佐证,有可能发现一些明显的博弈现象。此外,民意或顾客调查也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患者在急诊室的等待时间是英国医院的一个重要绩效指标,医院报告的数据和独立第三方患者调查得出的数据曾出现了30%的差距,这引发了社会争论并促进了等待时间计算方法的改进。[18]
第四,与时俱进进行绩效指标的动态调适优化。这包括随着施政理念、环境、社会需求和工作重点等的变化适时调整,也包括指标产生明显博弈行为时的适时调整。Courty和Marschke用委托代理理论论证适时调整的必要性:委托人设计指标时并不知道会导致哪些扭曲,但应用中会发现问题并修正,指标体系应处于一个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19] 这方面一个例子是美国的再就业培训。联邦政府的就业培训始于肯尼迪时代,20世纪80年代,培训市场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为强化责任,有关部门依法制定了一系列绩效标准,辅之以财务和其他形式的激励措施。最初的考核指标包括“单位成本”以提高管理者的效率意识,但很快发现这个指标鼓励培训机构的短期行为,如“挑奶皮”(只接受那些容易找到工作的人参加培训),不利于人力资本发展的长期需要。这一指标于1992年被取消。另一个结果类指标是“培训结束后的就业率”,1992年当局调整了这一指标,因为调研发现,培训机构工作重点放在介绍工作而非技能培训,这对受训者的长期能力产生负面影响。新指标是“培训结束后三个月的就业状况”,目的是提高他们的长期经济自立能力。1998年随着新法规的实施,这一指标改为“培训结束后六个月的就业状况”,同时增加了培训前后工资收入的比较,以反映培训工作产生的“增值”。此外,还增加了一个客户满意率指标,包括受培训者和雇主的满意度。[20]
最后是绩效目标的“模糊化”策略。Bevan和Hood提出,既然高度具体的目标会导致博弈行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对策就是增加指标的随机性或不确定性。如果被评估者“事先”只知道考核的维度而非具体衡量指标时,“事后”(即评估时)回头弄虚作假,许多策略就无法运用。这好比对超速驾驶行为的处罚,司机可能事先知道哪里安装了摄像头,但不知道特定摄像头是否在运行,也不知道超速多少会触发拍照,他们就会遵守交通规则。不过他们也承认,这种做法与绩效评估的其他功能存在矛盾。[21] 具体说,模糊化的绩效指标难以被公众接受,不利于发挥绩效指标的引导功能,也会使日常绩效信息的收集失去依据。
四、改进和完善激励机制
激励是绩效评估结果或绩效信息利用的方式之一,其他方式包括责任与灵活性交易、诊断与指导、绩效预算、制定来年绩效计划等。之所以专门讨论其中的激励机制,是因为激励机制被公认为博弈行为的重要致因。
激励结构与博弈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已为大量研究所证实。美国杜拉斯学区向“大幅提高学生阅读水平”的教师和校长提供450-1000美元的奖励,结果很快发现答案正确率和橡皮使用量出现了惊人的正相关。[22] Jacob等人的研究表明,学校作弊行为发生率与激励力度高度相关,激励的小幅调整也会带来作弊频率的相应变化。[23] 英国公立医院一个核心绩效指标是患者等待时间,这一指标在业内被称为P45指标(英国公共部门解雇雇员时会给当事人出具一个编号为P45的告知单)。惩罚措施力度最大,结果是相关数据最不可信:2005年的一个官方调查表明,37%的被访者相信政府数据是准确的,14%的人认为政府会诚实使用数据,而在公众认定的最不可信的六个数据系列中,医院等待时间数据赫然在列。[24] 也许这方面最系统的当属Fisher和Downes的研究,他们把激励机制分为比例奖励机制、小力度奖励机制、大力度奖励机制三个类型,结果发现随着奖励力度的逐步加大,不仅被评估者的作弊倾向会依次增加,而且作弊的不诚实程度(严重程度)会依次提高,从“隐瞒、误导”到“创造性归类、捏造数据”。他们还发现,重赏会引致作弊,边际状态下更甚:如果略做手脚(小幅度作弊)能使绩效档次跨越一个门槛,从而获得很大的利益,作弊可能就是不二选择。基于大量证据,Goodhart 提出了一个“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出于控制目的的压力一旦加剧,统计数据的可信性大厦就会轰然倒塌。另外一种表述是:某一指标成为大家竞相追逐的神灯,它就不再是一个有效度的指标。[25]
完善激励机制对绩效评估同样意味着一个尴尬的悖论:强化激励会引致弄虚作假,而淡化绩效激励会降低绩效评估和绩效管理的效用,激励“适度”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学者相关对策的探讨涉及理念和技术层面。理念层面,学术界推崇绩效评估的“3D模式”,即诊断(diagnosis)、发展(development)和(改进方案)设计(design),突出评估结果正面的建设性应用,避免施加过大的压力。这被归结为一句话:绩效评估就是要“欢呼成功,原谅失败”。制度层面的对策如针对团队的激励设计,避免目标具体到个人可能带来的破坏性竞争,而且团队集体作弊被曝光的风险也比较大。
上述结论和建议在绩效管理实践中都有所体现。这里仅介绍英美等国的“责任与灵活性交易”案例。这是一种制度化设计,通过授予高绩效单位更大的管理自主权,调动其提高绩效的积极性。我们以英国地方政府的财务管理权为例加以说明。英国地方政府支出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地方税(平均占65%)与中央转移支付(平均占35%)。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结果分ABCDE五个档次。获得A和B档次的地方政府享有自主决定地方税水平的权力,同时中央转移支付采取“一揽子拨款”或“打包拨款”的方式,其具体用途由地方政府自主决定。获得较低绩效档次的地方政府,年度地方税水平要经过中央审批,从而面临被“削帽尖”的风险。至于中央转移支付拨付方式,对C、D两档地方政府采取“分项拨款”的方式,用途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对E档地方政府则采取“分目拨款”方式,比分项拨款限制更细更严。[26]
五、加大对博弈行为的监督力度
在Bohte和Meier确认的“最有可能作弊”的四类组织中,监督力度弱的组织是其中之一。Fisher和Downes总结的引致作弊的四大情境因素中,包括了“作弊被发现的概率”和“受惩罚的严厉程度”。加强监督是博弈行为防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已为多数研究所证实,分歧只在于监督方式及其相对有效性。
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制定更多反作弊的正式规则来约束博弈行为的传统做法不可取。原因第一是,用规则来强化控制会引致规避控制的博弈行为,进而导致更多更详细的规则,组织生产力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会变得日益低下。第二,强化反作弊规则给被评估者传递一个信号,他们不值得信赖,这对士气和效能会产生负面影响。第三,规则不能消除其他因素导致的博弈动机,规则难以防范博弈行为的发生。[27]
加大监督力度包括两个方面:提高发现和确认博弈行为的能力;加大对已确认的作弊者的处罚力度。鉴于确认博弈行为是处罚的前提,并且是监督面临的最大难点,这里主要讨论提高确认博弈行为的能力。
第一个着力点是加强与绩效信息监督相关的组织和能力建设。这方面的关键是独立第三方评价审查,通过交叉审核和曝光形成威慑力。独立第三方首先指政府之外的公民社会团体和大众媒体,这些组织不仅独立承担公民满意度调查等,而且独立收集并公布一些客观绩效数据。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机构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运作的透明。
加强组织能力建设也涉及不同的政府部门,其“独立性”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议会专门委员会和隶属于立法机关的审计部门独立于行政机关;其他政府部门相对独立于业务主管部门。多元主体监督的理论基础是组织的冗余理论(redundancy theory),其核心是增加冗余度提高安全系数,或通过多重保险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学者们提出设立独立绩效信息管理机构或绩效数据审计机构等各种建议,实践中则表现为政府赋予多种机构调查核实绩效数据的权利和职责。以英国的医疗卫生系统为例,除审计办公室负有绩效信息审计职责外,内阁办公厅的服务供给小组(Prime Minister’s Delivery Unit)、财政部、公共卫生委员会(Healthcare Commission)、公共卫生改进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Improvement)等近20个机构都承担绩效数据的调查分析和审核职责,而且都发布自己的调查报告。这种叠床架屋的监督机构设置是为了避免先前发现的“审计漏洞”(audit hole),即单一监督机构被俘获从而和被监督部门合谋的现象。[28]
第二个着力点是改进完善监督的方式方法。首先是改变大张旗鼓定期检查的做法,更多采取不定期明察暗访的形式,在公共服务领域可扮演“神秘客户”(mystery shoppers)直接观察体验。其次,避免使用专业化晦涩语言,推进绩效指标简明化,使得绩效数据对用户更友好。最后是推进信息公开,改变绩效信息在政府内部的封闭循环,强化与民众面对面的交流沟通,通过社会监督提高博弈行为的曝光率。
第三个着力点是发现和确认博弈行为的具体技术。Bevan和Hood建议利用“历史趋势数据”对绩效信息进行核实检验。Hood提出完善信息管理中跨部门协同。比如说,福利部门办理某人不再领取失业救济的手续的同时,给就业部门的数据系统发出一个指令,否则这个人就不能登录进就业部门的再就业数据库。Jacob和 Levitt提出一个衡量作弊的创新技术,通过多种分析工具确认考试成绩的非正常波动和学生答案中的非正常现象。
六、总结与简要讨论
在对五种博弈行为主要防范策略讨论的基础上,本部分对其相互关系做一总结。借鉴Webley等人对逃税行为的WBAD分析模型(The Willing-Being-Able-Daring Model),Mears 和Webley针对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博弈行为,构建了一个分析应对模型,包括四类情况和相应的防范策略。第一是实事求是无作弊意愿(Not willing)的“圣人”,主要靠自我控制力做到诚实守信。对这类人时常提醒弄虚作假面临的风险,强化他们的自我规制力。第二种是有意愿但无能力(willing but not able)的“诚实的试探者”(Honest triers),尚未完全掌握作弊的门道。对这类人除提醒或警示外,还应灌输真实绩效数据对改进服务的重要意义,第三类是有意愿有能力但胆量不足(willing and able but not daring)的机会主义者,视情境偶尔踩边行事。对这类人要言明规则并酌情实施一定的处罚。第四类属于意愿、能力、胆量齐备的“理性作弊狂”(rational maniacs),对这类人要加强监管,视情节实施严厉处罚,必要时绳之以法。当然,上述所有对策都以发现并确认博弈行为为前提。[29]
借鉴意愿、能力、胆量分析模型,我们把博弈行为的五种防范策略归为三类:“提高评估体系认同度”和“完善激励机制”主要解决的是“意愿”问题;“优化绩效指标体系”主要解决“能力”问题,即压缩绩效指标可注水或可操纵空间,使那些“诚实的试探者”难以付诸行动;强化监督力度则针对“胆量”问题,提高作弊的曝光率和加大处罚力度,使作弊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角度看不划算,迫使他们诚实守信。换言之,使诚实守信成为多数“理性经济人”在外部约束下唯一理性的选择。社会规范建设的归类比较复杂,应该说是四个防范策略共同作用的理想状态,即通过综合努力,造成一种不愿、不能、不敢弄虚作假的社会大气候。也许基于这一点,它被视为博弈行为的首要防范策略。
信息失真是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人为弄虚作假则是信息失真的重要原因,探讨博弈行为的防范之道同样显得必要和迫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际理论研究成果和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周志忍,徐艳晴.绩效评估中的博弈行为及其致因研究:国际文献综述[J].中国行政管理,2013(12).
[2][10] Fisher, Colin and Bernadette Downes.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Metric Manipul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Business Ethics: A European Review, Vol. 17, No. 3, 2008.
[3] Goldsen, R., Rosenberg, M., Williams, R., & Suchman, E. What College Students Think. Oxford, England: D. Van Nostrand,1960.
[4] Martin, Amy. Does Religion Buffer Cheating?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2013.
[5] Longenecker, J. G., McKinney, J. A., & Moore, C. A. Religious Intensity,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and Business Ethics: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4(55).
[6] 凌文栓,郑晓明,方俐洛.社会规范的跨文化比较[J].心理学报,2003(2).
[7] Reno, Raymond R.,Cialdini, Robert B.,and Kallgren, Carl. The Transsituational Influence of Social Norm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3(64).
[8] 李本森.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0(5).
[9] Muraven, M., Tice, D. M., and Baumeister, R. F. Self-control as a Limited Resource: Regulatory Depletion Patter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4, 774-789.
[11]Armstrong, Michae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London: Kogan Page Limited,1994. pp. 21-22.
[12]Modell, S.,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a Study of Managerial Responses to Public Sector Reform.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Vol. 12, No. 4, 2001.
[13]Benabou. Charles and Rapha Benabou. Establishing a Formal Mentoring Program for Organizational Success. National Productivity Review, Vol. 18, No 2,1999.
[14][16][27] Bohte, John and Kenneth J. Meier. Goal Displacement: Assessing the Motivation for Organizational Chea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March/April 2000, Vol. 60, No. 2, pp. 173-182.
[15] 周志忍:当代政府管理的新理念[J].北京大学学报,2005(3).
[17] Fast, Norman and Norman Berg. The Lincoln Electric Compan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 #376-028.
[18][24] Hood, Christopher. Gaming in Targetworld: The Targets Approach to Managing British Public Servic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July/August 2006.
[19] Courty, Pascal and Gerald Marschke. Dynamics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ystems.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19, No. 2, 2003.
[20][23] Jacob, Brian A. and Steven D. Levitt, Rotten Apple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teacher cheating, Working Paper 9413, http://www.nber.org/papers/w9413.
[21][28] Bevan, Gwyn and Christopher Hood. What’s Measured is What Matters: Targets and Gaming in the English Public Health Care System.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84, No. 3, 2006.
[22] Garcia, Joseph. In Dallas: District Ranks School by How Much They Improve on Traditional Tests. Catalyst,1995(11).
[25] Goodhart, C. A. E. Monetary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UK Experience. London: Macmillan,1984.
[26]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August 2002), Results–Oriented Cultures: Insights for U.S. Agenc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itiatives.
[29] Mears, Alex and Paul Webley. Gaming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Health Care: Parallels with Tax Compliance.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 Policy, Vol. 15,No. 4, 2010.
Countermeasures to Gaming i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easurement:Theories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Zhou Zhiren Xu Yanqing
[Abstract]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has long been perplexed by information distortion and gaming behavior is a main cause for this. Consequently, motivations for cheating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have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This paper provides a primary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anti-cheating practices overseas in an attempt to facilitat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he fight against gaming in China. The main anti-cheating strategies covered include construction of favourable social norms,strengthening external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enhancing approbation among staff of th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ystem, dynamic optimization of performance measures, and improvement of motivation mechanisms.
[Keywords]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formation distortion, gaming behavior
[Authors]Zhou Zhiren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Xu Yanqing is Postdoctoral Fellow at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原文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6期)

